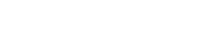伙房内,一顿午膳在沉默的氛围中吃完!
宗泽唤来衙役把桌上的碗筷收拾了,让他们远远地退开。靠在椅子上,上下打量着对面的孙新。一欢老眼非但不浑浊,反而非常清澈透亮倍有神。
眼神闪烁不定,老头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如宗泽说的那样,他找孙新就是为了毛家之事而来。他外出办完事,回到登州城,就知道发生了不少大事。如毛家被人灭门,登州有了兵马提辖等。
这段时间宗泽四处打探,明察暗访,了解毛家被灭的始末缘由,可东拼西凑得出的结果令他知道大概。毛家坏事做尽,陷害他人,的确勾结强人。
除此之外,也有诸多疑惑,令宗泽百思不得其解。偏偏这家伙又非常固执,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。这不,当事人孙新归来后,次日便闻讯找来。
“老爷子,你有话就说,下官还要忙着招兵训练!”孙新被这个死老头看得有些发毛,主动打破僵局。他的确有很多事情要做,毕竟太平日子不会太久。得趁着安稳时快速发展自身,没时间浪费。
“好好好……”宗泽回过神来,尴尬地笑了几声。在身上摸了半天,从袖口里掏出一根银制的牙签来。一边剔着牙齿,一边强调着说道:“重光,请你来只是想询问一番,就当成私下你我闲聊。”
“老爷子你有事就说,知无不言。”孙新笑容以对。
“好!”宗泽说了声,往旁边地上呸了一口,正色道:“毛家在登州盘踞了几代人上百年,也算是排名靠前的地主豪强。入库的钱财和登记的田地数目不对,老头子认为大有出入,所以想要查清楚。”
“通判大人,此事绝无任何异常!”孙新脸色变得严肃:“毛家勾结水泊梁山,暗中资助了不少钱粮。具体数目无可查清,但绝对不少,当时又有强人一把火烧了粮仓,趁乱掳掠走了毛家不少财宝。”
说实话,孙新从知道登州通判是宗泽这个老头后,就一直琢磨着这套说辞,来应付对方的询问追查。如今派上用场,他说得滔滔不绝,言辞恳切。
“再说了,在这件事之前毛家还因为一只大虫,勾结官府王孔目,陷害我解珍,解宝两个兄弟,买通包吉想在死牢中谋害,毛仲义那小子毛手毛脚不干净。又偷我家传家宝物,后来这件事闹到官府去了。他毛家当众表示要赔偿我三千两黄金……”
“多少?三千两黄金?”宗泽眼珠子瞪圆。
“不错,就是这么多,白纸黑字,我家还留有字据为证。大人要是不信,随时到我家,我拿给你看。”孙新满脸正气,言之凿凿,不像是作假。
他见老头眼神闪烁,像是听得云山雾罩,索性把解家兄弟遭遇陷害的事情,到官府请太守裁断,然后在街上遇到袭击,最后下令去毛家捉拿犯人的事情详细说来,当然该说的说,不该说的不说。整个故事链早就打磨的紧凑,没有丝毫破绽可言。
“原来是这样!”宗泽听到孙新把事情经过全部说来,只觉得与自己东拼西凑了解到的情况大同小异,顿时有很多疑惑之处迎刃而解,下意识呢喃。
不过,随着老头一思索,又觉得有些地方不对。可哪里不对,一时半会却说不清楚,眉头不禁皱起来。一遍遍推敲孙新说的话,想找出其中的漏洞,破绽,可最后结果一无所获,非常紧凑无误。
“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不简单呐!”宗泽看着对面俊朗不凡的年轻军官,莫名有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。
“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!毛家数万石粮食付之一炬。钱财也只剩下这么多入库,良田也被卖出……”孙新滔滔不绝地说完,总结过后便不再多言。
宗泽从思索中回过神,意味深长地笑了笑:“据老夫所知,毛家至少有四万亩良田,与卖出的数……”
“没有那么多,只有三万多亩。”孙新笑着摆手打断:“大人可以查阅田地转卖记录,一年多前,毛家将一批比较贫瘠的田地卖掉,总数量就这么多。”
“纵使数量对得上,可这卖得的钱财……”
孙新体会到老头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阴沉着脸说:“这个由于地头蛇联合,卖的价不高,二是其中五千亩属下半价买下。也算在登州城安家落户。下官近来屡立功劳,半价购买置办产业情有可原。”
宗泽被说得一愣一愣的,可随即又提出疑问来:“按北宋律法,一亩田五两银子左右,两万多亩良田……”
孙新实在受不了这个老头揣着明白装糊涂,固执地追问。直接语气加重的打断:“大人,不要再说下去了,有时候追根溯源反而没好处。您老的精神和尽职尽责的态度令小子钦佩不已,奈何时不我待,在浑浊的世道之中,不应该太过明白,你知道就好,有时候假糊涂,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当差办事的谁没有家人,沾沾油水,过一个好年。”
“你……,哎,你说得对。”宗泽被说得无语凝噎,随即怔怔地看着孙新无奈地叹气。他的确明白了,不仅明白对方劝说自己,也明白的确是有鬼哟!想想也是这么一大块肥肉,贪婪的人怎会放过?
不单单主官刘豫贪没钱财,大小官吏也从中获益。怪不得这段时间查不出什么来,口风也一致统一。感情是整个登州官场因为毛家覆灭而瓜分利益。他宗泽再固执再牛叉,如何与所有人为敌乎?
孙新也盯着头发花白的老头,无奈地苦笑:“老爷子,知道却不说破,不伤天害理,睁只眼闭只眼。有人吃饱了能干点实事,也能为百姓着想。如能够接受建议,招募地方军队,防范海中的威胁。”
“是啊!”宗泽深有同感,又问道:“敢问重光之志?”
孙新直勾勾地看着宗泽,不掩饰自己的野心:“溜须拍马。装孙子往上爬,当大官,手中有兵权。”
“嗯,你是想?”宗泽眼睛眯起,警惕地看着孙新。
孙新感受到一股警惕以及淡淡的敌意,没有在意。他知道这是一个忠于朝廷的老顽固,不是轻易说通的。目光不躲不闪,坦坦荡荡,朝南方拱拱手:“老爷子,你的担心多余,据说圣上主张联金灭辽。”
“联金灭辽?”宗泽喃喃自语,老脸上闪过无奈之色。他当然知道这件事,半年前特使从登州乘船出发。又紧盯着孙新:“重光,那你如何看待此事?”
“国家大事,我等没有资格议论。”孙新着重强调,随即反问道:“辽国都打不过,面对把辽国打得节节败退,覆灭数十万军队的金国,又当如何?”
“哎!”宗泽失神片刻,仰天长叹!
孙新在茶水中沾湿手指,在桌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地形图:“我个人觉得,真的把辽国灭了。同盟国金国会立刻撕破脸皮。幽州这些险关肯定会被金人占据,等他们消化完辽国,我大宋处境堪忧啊!”
宗泽看着地形图上圈出来的险关,止不住连连称赞:“是极是极,老夫也是这样想的,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我们应该趁着辽国还能抵挡几年,整顿各地军队准备着,而不是急切地将之绞杀引来更可怕的敌人了。故而联金灭辽这个策略是愚……。”
“老爷子,慎言。”孙新赶忙打断宗泽的口不择言。看看四周见没有人,也不想再继续谈论,提议:“此地非说话之地,有时间老爷子可以找我来探讨。”
“好好好,是我失言了。”遇到知己,宗泽很高兴。
“对了,老爷子,毛家之事就此终结,他们的确勾结梁山泊,意图谋反。眼下这种算是最好的处置。你却可以以这个借口,隔三差五的来纠缠于我。”
“哎,老头子心中有数!”宗泽满脸无奈。
“只要不伤天害理,得过且过!”孙新也露出苦笑。随即又跟这个顽固的老头闲聊一会,便起身离开伙房,最后双方莫名争吵起来,闹得不欢而散!
宗泽唤来衙役把桌上的碗筷收拾了,让他们远远地退开。靠在椅子上,上下打量着对面的孙新。一欢老眼非但不浑浊,反而非常清澈透亮倍有神。
眼神闪烁不定,老头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如宗泽说的那样,他找孙新就是为了毛家之事而来。他外出办完事,回到登州城,就知道发生了不少大事。如毛家被人灭门,登州有了兵马提辖等。
这段时间宗泽四处打探,明察暗访,了解毛家被灭的始末缘由,可东拼西凑得出的结果令他知道大概。毛家坏事做尽,陷害他人,的确勾结强人。
除此之外,也有诸多疑惑,令宗泽百思不得其解。偏偏这家伙又非常固执,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。这不,当事人孙新归来后,次日便闻讯找来。
“老爷子,你有话就说,下官还要忙着招兵训练!”孙新被这个死老头看得有些发毛,主动打破僵局。他的确有很多事情要做,毕竟太平日子不会太久。得趁着安稳时快速发展自身,没时间浪费。
“好好好……”宗泽回过神来,尴尬地笑了几声。在身上摸了半天,从袖口里掏出一根银制的牙签来。一边剔着牙齿,一边强调着说道:“重光,请你来只是想询问一番,就当成私下你我闲聊。”
“老爷子你有事就说,知无不言。”孙新笑容以对。
“好!”宗泽说了声,往旁边地上呸了一口,正色道:“毛家在登州盘踞了几代人上百年,也算是排名靠前的地主豪强。入库的钱财和登记的田地数目不对,老头子认为大有出入,所以想要查清楚。”
“通判大人,此事绝无任何异常!”孙新脸色变得严肃:“毛家勾结水泊梁山,暗中资助了不少钱粮。具体数目无可查清,但绝对不少,当时又有强人一把火烧了粮仓,趁乱掳掠走了毛家不少财宝。”
说实话,孙新从知道登州通判是宗泽这个老头后,就一直琢磨着这套说辞,来应付对方的询问追查。如今派上用场,他说得滔滔不绝,言辞恳切。
“再说了,在这件事之前毛家还因为一只大虫,勾结官府王孔目,陷害我解珍,解宝两个兄弟,买通包吉想在死牢中谋害,毛仲义那小子毛手毛脚不干净。又偷我家传家宝物,后来这件事闹到官府去了。他毛家当众表示要赔偿我三千两黄金……”
“多少?三千两黄金?”宗泽眼珠子瞪圆。
“不错,就是这么多,白纸黑字,我家还留有字据为证。大人要是不信,随时到我家,我拿给你看。”孙新满脸正气,言之凿凿,不像是作假。
他见老头眼神闪烁,像是听得云山雾罩,索性把解家兄弟遭遇陷害的事情,到官府请太守裁断,然后在街上遇到袭击,最后下令去毛家捉拿犯人的事情详细说来,当然该说的说,不该说的不说。整个故事链早就打磨的紧凑,没有丝毫破绽可言。
“原来是这样!”宗泽听到孙新把事情经过全部说来,只觉得与自己东拼西凑了解到的情况大同小异,顿时有很多疑惑之处迎刃而解,下意识呢喃。
不过,随着老头一思索,又觉得有些地方不对。可哪里不对,一时半会却说不清楚,眉头不禁皱起来。一遍遍推敲孙新说的话,想找出其中的漏洞,破绽,可最后结果一无所获,非常紧凑无误。
“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不简单呐!”宗泽看着对面俊朗不凡的年轻军官,莫名有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。
“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!毛家数万石粮食付之一炬。钱财也只剩下这么多入库,良田也被卖出……”孙新滔滔不绝地说完,总结过后便不再多言。
宗泽从思索中回过神,意味深长地笑了笑:“据老夫所知,毛家至少有四万亩良田,与卖出的数……”
“没有那么多,只有三万多亩。”孙新笑着摆手打断:“大人可以查阅田地转卖记录,一年多前,毛家将一批比较贫瘠的田地卖掉,总数量就这么多。”
“纵使数量对得上,可这卖得的钱财……”
孙新体会到老头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阴沉着脸说:“这个由于地头蛇联合,卖的价不高,二是其中五千亩属下半价买下。也算在登州城安家落户。下官近来屡立功劳,半价购买置办产业情有可原。”
宗泽被说得一愣一愣的,可随即又提出疑问来:“按北宋律法,一亩田五两银子左右,两万多亩良田……”
孙新实在受不了这个老头揣着明白装糊涂,固执地追问。直接语气加重的打断:“大人,不要再说下去了,有时候追根溯源反而没好处。您老的精神和尽职尽责的态度令小子钦佩不已,奈何时不我待,在浑浊的世道之中,不应该太过明白,你知道就好,有时候假糊涂,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当差办事的谁没有家人,沾沾油水,过一个好年。”
“你……,哎,你说得对。”宗泽被说得无语凝噎,随即怔怔地看着孙新无奈地叹气。他的确明白了,不仅明白对方劝说自己,也明白的确是有鬼哟!想想也是这么一大块肥肉,贪婪的人怎会放过?
不单单主官刘豫贪没钱财,大小官吏也从中获益。怪不得这段时间查不出什么来,口风也一致统一。感情是整个登州官场因为毛家覆灭而瓜分利益。他宗泽再固执再牛叉,如何与所有人为敌乎?
孙新也盯着头发花白的老头,无奈地苦笑:“老爷子,知道却不说破,不伤天害理,睁只眼闭只眼。有人吃饱了能干点实事,也能为百姓着想。如能够接受建议,招募地方军队,防范海中的威胁。”
“是啊!”宗泽深有同感,又问道:“敢问重光之志?”
孙新直勾勾地看着宗泽,不掩饰自己的野心:“溜须拍马。装孙子往上爬,当大官,手中有兵权。”
“嗯,你是想?”宗泽眼睛眯起,警惕地看着孙新。
孙新感受到一股警惕以及淡淡的敌意,没有在意。他知道这是一个忠于朝廷的老顽固,不是轻易说通的。目光不躲不闪,坦坦荡荡,朝南方拱拱手:“老爷子,你的担心多余,据说圣上主张联金灭辽。”
“联金灭辽?”宗泽喃喃自语,老脸上闪过无奈之色。他当然知道这件事,半年前特使从登州乘船出发。又紧盯着孙新:“重光,那你如何看待此事?”
“国家大事,我等没有资格议论。”孙新着重强调,随即反问道:“辽国都打不过,面对把辽国打得节节败退,覆灭数十万军队的金国,又当如何?”
“哎!”宗泽失神片刻,仰天长叹!
孙新在茶水中沾湿手指,在桌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地形图:“我个人觉得,真的把辽国灭了。同盟国金国会立刻撕破脸皮。幽州这些险关肯定会被金人占据,等他们消化完辽国,我大宋处境堪忧啊!”
宗泽看着地形图上圈出来的险关,止不住连连称赞:“是极是极,老夫也是这样想的,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我们应该趁着辽国还能抵挡几年,整顿各地军队准备着,而不是急切地将之绞杀引来更可怕的敌人了。故而联金灭辽这个策略是愚……。”
“老爷子,慎言。”孙新赶忙打断宗泽的口不择言。看看四周见没有人,也不想再继续谈论,提议:“此地非说话之地,有时间老爷子可以找我来探讨。”
“好好好,是我失言了。”遇到知己,宗泽很高兴。
“对了,老爷子,毛家之事就此终结,他们的确勾结梁山泊,意图谋反。眼下这种算是最好的处置。你却可以以这个借口,隔三差五的来纠缠于我。”
“哎,老头子心中有数!”宗泽满脸无奈。
“只要不伤天害理,得过且过!”孙新也露出苦笑。随即又跟这个顽固的老头闲聊一会,便起身离开伙房,最后双方莫名争吵起来,闹得不欢而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