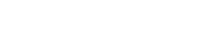彦霖被哥哥的举动吓坏了,她只是想让哥哥吓唬吓唬金美丽,让她以后别太嘚瑟,别再抢自己的风头,却不想哥哥下手这么狠,竟然把女孩视作极为珍贵的长发给剪掉了。
“不要,不要啊哥,”彦霖见哥哥还要继续剪金美丽的头发,连忙惊呼制止,“不要再剪她的头发了。”
彦霖哥哥见妹妹吓坏的样子,不屑地说:“瞅你那损样,不是你让我吓唬她的吗,咋的,还没下重手呢,你就尿裤子了?”
彦霖说:“我只是让你吓唬她,警告她,没让你剪她头发啊!”
“你们小姑娘就是难伺候。”彦霖哥哥收起剪子,白了彦霖一眼。
接着,彦霖哥哥用彩色油笔,在金美丽脸上画了起来,“你不是长得漂亮吗,哥给你化化妆,让你更漂亮些!”
他的画笔在金美丽脸上胡乱涂抹起来,把她化成了一个大花脸,然后和伙伴扬长而去。
下午上课,班长点名,没有见到金美丽。
班主任就很生气,这个金美丽一点规矩也不懂,有事不来上课,难道不能请个假吗?
可是,当班长点名点到窦芍药时,也没听到她喊报到。
老师就更生气了,“这是要造反啊,一个没来不请假,窦芍药也不请假就旷课,这还了得?”
班主任问扈红,“窦芍药咋回事,为啥旷课?”
扈红站在那里不知所以然,她也不知道,窦芍药为啥没来上课?
班主任就让她晚上放学后,去窦芍药家看看,为啥旷课?
其实,窦芍药是不可能旷课的,这天中午她突然犯困,就歪在炕上睡了一小会儿。等她被弟弟都英俊吵醒,还有十几分钟就该打上课铃声了。
“黑丫”穿上鞋子就往学校跑。
在半路上,她遇见了被剪掉马尾辫,脸上画得像大花猫似的金美丽,一边呜呜哭着,一边往家走。
“黑丫”觉得纳闷,就停住脚步问她,“是谁干的?”
金美丽不敢说,只是哭,一个劲儿地哭。
“你再这样,没人搭理你了,快说啊!”
“黑丫”急了,就朝她喊了起来。
上次“黑丫”关键时候仗义出手,为自己解围救困,金美丽心里一直感激她,见她恼了,就把刚才的遭际说了一遍。
“死彦霖!太可恨了!”
“黑丫”气愤至极,狠狠地剁脚。
“你咋整呀,脸被画成这样,没法上课了呀?”
“黑丫”听到了上课铃声,焦急地说,“要迟到了,我先走了,你赶紧回家洗洗脸吧。”
“我不敢回家。”金美丽哭着说。
“黑丫”想想也是,她要是这样回家,父母还不得打她骂她啊!
“唉,彦霖太恨人了。”
“黑丫”拽着金美丽来到河边,帮她洗脸上的油彩。
可是洗了好一会儿,也没洗净油彩,相反越洗脸上越花花——油彩油性太大,清水根本洗不掉。
金美丽见状,又呜呜哭了起来,“咋整呀,我的脸咋整呀?”
“黑丫”脱掉鞋子,光脚走进河里。脚丫试探着,找到淤泥河底,弯腰捞起一把淤泥走回来。
“黑丫”用淤泥将金美丽脸上糊了一层,黑黑的,腻腻的,特别像现在女士涂在脸上的火山灰面膜。
十几分钟后,“黑丫”让金美丽用河水把脸上的淤泥洗干净,奇迹出现了,她脸上的油彩竟然不见了。
金美丽惊奇地看着河水映现出的自己的白皙美丽的面孔,简直不敢相信,一层看似埋汰、甚至泛着腥臭味儿的淤泥,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功效?
“黑丫”见怪不怪地笑了,说:“你瞪那么大眼睛看我干啥,你不知道,淤泥去油污的效果老好了,以前爸爸和妈妈洗衣服,就是用这种办法洗掉妹妹洒在衣服上的油污的,奇效!”
“黑丫”见金美丽又恢复成那个美丽、漂亮的女孩儿,就拽着她去上课。
金美丽不想去上课了,她的眼睛里布满忧郁、哀伤和胆怯,右手不自然地在脑后摸着。
那里的马尾辫不见了。
“黑丫”知道,她为失去马尾辫而伤心,突然想,金美丽失去了马尾辫,万一伤心过度,投河了咋办?
于是她一咬牙说,“好吧,我下午也不去上课了,陪着你。”
“那,你无故旷课,老师要惩罚你的。”金美丽抬起美丽的眸子,不安地说。
“没事,顶多被老师骂一顿。”
“黑丫”抓住金美丽的手,朝下游的柳树丛里走去。
柳树丛前的河滩上,有一片金色的细沙滩。“黑丫”和金美丽并肩躺在沙滩上,唠了一下嗑。
估计快到放学时间了,她俩才手牵手走出柳树丛。
晚饭前,扈红急匆匆来到“黑丫”家,把她拽出院门,问她下午跑哪野去了,为啥旷课?
“黑丫”就把金美丽的遭际跟她说了。
扈红属于炮仗脾性,听说后当即就炸了,“太缺德了,彦霖太缺德了!”
“黑丫”说:“是挺气人的,哪有啥仇恨啊,非得剪掉人家的头发!这不是欺负人嘛。”
“你打算咋报复彦霖?”扈红问道。
“还能咋报复她,明天上课告诉老师呗。”“黑丫”说。
“告诉老师,顶多批评她一顿就得了,这样太便宜彦霖了,不行,这口气我咽不下去!”扈红摇头说。
“那你说咋办?”“黑丫”问。
“你别管了,我就问你,想不想给金美丽出气吧?”扈红瞪着眼珠子问。
“想啊,可是,可是我们不能违反学校纪律啊……”
“黑丫”为难地说道。
“这你就别管了,好汉做事好汉当!”扈红说完,转身迈着大步铿锵有力地走了。
第二天第二节课是体育课,第三节课是语文课。
语文老师是班主任,是个和蔼的大龄未婚女人。她跟同学们互相问好后,转身在黑板上写这节课要学习的生字。
突然,彦霖发出一声惊叫,桌子上的铅笔和书本,哗啦掉在地上。
语文老师转身,看见彦霖脸色煞白,满眼是泪地站在课桌外,右手在不断地甩动着,似乎手上沾染了什么不洁的脏东西。
同学们也炸锅了,不顾课堂纪律,纷纷跑过去瞧热闹。
语文老师扒拉开男同学脑袋,挤过去,看见一个男同学手里,拎着一只幼鸟。
这只幼鸟刚出蛋壳,还没睁开眼睛呢,身上还没长羽毛,皱皱巴巴的皮囊,丑陋得像个怪物。
原来,有人竟然偷偷将刚出壳的幼鸟,放进彦霖的书包里了。
彦霖显然吓坏了,身子一直在颤抖,眼泪一直在流。
语文老师知道是恶作剧,追问了几个淘小子,都不承认“作案”。老师问彦霖,知不知道是谁干的?得罪了谁?
彦霖本能地想到金美丽,昨天哥哥捉弄了她,如果要说嫌疑人,金美丽最有可能“涉嫌”报复。
可是金美丽今天没来,请假了。
彦霖就有些蒙圈了。
到底是谁干的?
语文老师破了一节课案,也没找到“真凶”。
“黑丫”心里明镜似的,她去看扈红。
扈红一脸的幸灾乐祸,朝她挤眼睛。
“黑丫”剜了扈红一眼,意思是你做得太过了,这样的恶作剧有点不讲究。
扈红嘴巴下沉,嘴唇下撇,意思是你现在说啥也没用了,我已经恶搞完彦霖,她遭到报复了。
徐翠翠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,时而清醒,时而糊涂。
而这段时间,窦青山也更加地忙碌起来,他不仅要搞北黄芪种植试验,还被县林业局抽调出去,与局里的几位土专家一起,给率宾县西部的几个林场“诊脉”。
哪里发生了严重的松线毛虫病,导致大面积人工松树林枯死。
父亲不在的这十几天,“黑丫”简直不堪重负,不仅要安抚母亲的情绪,还要照顾妹妹窦红英和弟弟窦英俊窦。
窦红英在林场幼儿园,明年就要上小学一年级。而窦英俊才上幼儿园小班,每天清晨,别的孩子还在睡梦中,“黑丫”就要起床帮母亲做早饭。
早饭做好后,“黑丫”要掀开妹妹弟弟的被子,把他们从热被窝里拽出来。
然后督促他们洗脸吃饭,然后她提前把妹妹和弟弟送到幼儿园,再急行军似的跑到学校。
十几天后,父亲回到朝阳林场,下了车,他就急慌慌地朝家里奔。
这些天来,他几乎吃不好睡不好,就是惦记家里的情况,他感觉家里一定会乱成一团,会堆满孩子们未洗的衣服,甚至发出刺鼻的馊味儿。
窦青山不仅惦记老婆的病情反复严重,还惦记几个小孩子的吃喝拉撒。
他甚至向上苍祈祷,离开家的这些日子,徐翠翠千万不要发病,不要给“黑丫”添乱,不然这个才8岁的女孩就太难了。
窦青山急迫地推开家门。
徐翠翠正坐在梳妆台前梳洗长头发,显然她刚刚洗完头,正用木梳一点点仔细地梳理。
“你咋才回来呢,青山,这些天你去哪了,我等你等得好苦啊!”
徐翠翠惊喜地转过头,脸上表情由喜转悲。
窦青山一边安慰妻子,一边寻找他想象中的馊了的孩子们脱下来的衣服。
可他从这屋转到那屋,再转到仓房,也没找到那堆脏衣服。
他再看屋里,看炕上,看厨房,都是井井有条,干干净净,所有的东西都置放的规规矩矩,板板正正。
窦青山心里就涌过一阵暖流,他突然眼眶一热,觉得女儿“黑丫”实在太能干了,她太不容易了。
大女儿才8岁啊,她幼小的年记,弱小的肩膀,竟然扛起了这个家,而且比自己在家时拾掇的还利索、还干净,而且一切都是那么规整……
既然家里没有杂乱无章,没有乱成一锅粥,窦青山就放心了,她简单安抚徐翠翠几句,骑上摩托车去了西山苗圃。
可是他万万没想到,晚上回来时,家里出现了令他心碎愤怒的一幕,他挥起笤帚就把徐翠翠和“黑丫”暴揍了一顿。
愤怒使得窦青山失去了理智,愤怒的他,把笤帚都打碎了!
“不要,不要啊哥,”彦霖见哥哥还要继续剪金美丽的头发,连忙惊呼制止,“不要再剪她的头发了。”
彦霖哥哥见妹妹吓坏的样子,不屑地说:“瞅你那损样,不是你让我吓唬她的吗,咋的,还没下重手呢,你就尿裤子了?”
彦霖说:“我只是让你吓唬她,警告她,没让你剪她头发啊!”
“你们小姑娘就是难伺候。”彦霖哥哥收起剪子,白了彦霖一眼。
接着,彦霖哥哥用彩色油笔,在金美丽脸上画了起来,“你不是长得漂亮吗,哥给你化化妆,让你更漂亮些!”
他的画笔在金美丽脸上胡乱涂抹起来,把她化成了一个大花脸,然后和伙伴扬长而去。
下午上课,班长点名,没有见到金美丽。
班主任就很生气,这个金美丽一点规矩也不懂,有事不来上课,难道不能请个假吗?
可是,当班长点名点到窦芍药时,也没听到她喊报到。
老师就更生气了,“这是要造反啊,一个没来不请假,窦芍药也不请假就旷课,这还了得?”
班主任问扈红,“窦芍药咋回事,为啥旷课?”
扈红站在那里不知所以然,她也不知道,窦芍药为啥没来上课?
班主任就让她晚上放学后,去窦芍药家看看,为啥旷课?
其实,窦芍药是不可能旷课的,这天中午她突然犯困,就歪在炕上睡了一小会儿。等她被弟弟都英俊吵醒,还有十几分钟就该打上课铃声了。
“黑丫”穿上鞋子就往学校跑。
在半路上,她遇见了被剪掉马尾辫,脸上画得像大花猫似的金美丽,一边呜呜哭着,一边往家走。
“黑丫”觉得纳闷,就停住脚步问她,“是谁干的?”
金美丽不敢说,只是哭,一个劲儿地哭。
“你再这样,没人搭理你了,快说啊!”
“黑丫”急了,就朝她喊了起来。
上次“黑丫”关键时候仗义出手,为自己解围救困,金美丽心里一直感激她,见她恼了,就把刚才的遭际说了一遍。
“死彦霖!太可恨了!”
“黑丫”气愤至极,狠狠地剁脚。
“你咋整呀,脸被画成这样,没法上课了呀?”
“黑丫”听到了上课铃声,焦急地说,“要迟到了,我先走了,你赶紧回家洗洗脸吧。”
“我不敢回家。”金美丽哭着说。
“黑丫”想想也是,她要是这样回家,父母还不得打她骂她啊!
“唉,彦霖太恨人了。”
“黑丫”拽着金美丽来到河边,帮她洗脸上的油彩。
可是洗了好一会儿,也没洗净油彩,相反越洗脸上越花花——油彩油性太大,清水根本洗不掉。
金美丽见状,又呜呜哭了起来,“咋整呀,我的脸咋整呀?”
“黑丫”脱掉鞋子,光脚走进河里。脚丫试探着,找到淤泥河底,弯腰捞起一把淤泥走回来。
“黑丫”用淤泥将金美丽脸上糊了一层,黑黑的,腻腻的,特别像现在女士涂在脸上的火山灰面膜。
十几分钟后,“黑丫”让金美丽用河水把脸上的淤泥洗干净,奇迹出现了,她脸上的油彩竟然不见了。
金美丽惊奇地看着河水映现出的自己的白皙美丽的面孔,简直不敢相信,一层看似埋汰、甚至泛着腥臭味儿的淤泥,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功效?
“黑丫”见怪不怪地笑了,说:“你瞪那么大眼睛看我干啥,你不知道,淤泥去油污的效果老好了,以前爸爸和妈妈洗衣服,就是用这种办法洗掉妹妹洒在衣服上的油污的,奇效!”
“黑丫”见金美丽又恢复成那个美丽、漂亮的女孩儿,就拽着她去上课。
金美丽不想去上课了,她的眼睛里布满忧郁、哀伤和胆怯,右手不自然地在脑后摸着。
那里的马尾辫不见了。
“黑丫”知道,她为失去马尾辫而伤心,突然想,金美丽失去了马尾辫,万一伤心过度,投河了咋办?
于是她一咬牙说,“好吧,我下午也不去上课了,陪着你。”
“那,你无故旷课,老师要惩罚你的。”金美丽抬起美丽的眸子,不安地说。
“没事,顶多被老师骂一顿。”
“黑丫”抓住金美丽的手,朝下游的柳树丛里走去。
柳树丛前的河滩上,有一片金色的细沙滩。“黑丫”和金美丽并肩躺在沙滩上,唠了一下嗑。
估计快到放学时间了,她俩才手牵手走出柳树丛。
晚饭前,扈红急匆匆来到“黑丫”家,把她拽出院门,问她下午跑哪野去了,为啥旷课?
“黑丫”就把金美丽的遭际跟她说了。
扈红属于炮仗脾性,听说后当即就炸了,“太缺德了,彦霖太缺德了!”
“黑丫”说:“是挺气人的,哪有啥仇恨啊,非得剪掉人家的头发!这不是欺负人嘛。”
“你打算咋报复彦霖?”扈红问道。
“还能咋报复她,明天上课告诉老师呗。”“黑丫”说。
“告诉老师,顶多批评她一顿就得了,这样太便宜彦霖了,不行,这口气我咽不下去!”扈红摇头说。
“那你说咋办?”“黑丫”问。
“你别管了,我就问你,想不想给金美丽出气吧?”扈红瞪着眼珠子问。
“想啊,可是,可是我们不能违反学校纪律啊……”
“黑丫”为难地说道。
“这你就别管了,好汉做事好汉当!”扈红说完,转身迈着大步铿锵有力地走了。
第二天第二节课是体育课,第三节课是语文课。
语文老师是班主任,是个和蔼的大龄未婚女人。她跟同学们互相问好后,转身在黑板上写这节课要学习的生字。
突然,彦霖发出一声惊叫,桌子上的铅笔和书本,哗啦掉在地上。
语文老师转身,看见彦霖脸色煞白,满眼是泪地站在课桌外,右手在不断地甩动着,似乎手上沾染了什么不洁的脏东西。
同学们也炸锅了,不顾课堂纪律,纷纷跑过去瞧热闹。
语文老师扒拉开男同学脑袋,挤过去,看见一个男同学手里,拎着一只幼鸟。
这只幼鸟刚出蛋壳,还没睁开眼睛呢,身上还没长羽毛,皱皱巴巴的皮囊,丑陋得像个怪物。
原来,有人竟然偷偷将刚出壳的幼鸟,放进彦霖的书包里了。
彦霖显然吓坏了,身子一直在颤抖,眼泪一直在流。
语文老师知道是恶作剧,追问了几个淘小子,都不承认“作案”。老师问彦霖,知不知道是谁干的?得罪了谁?
彦霖本能地想到金美丽,昨天哥哥捉弄了她,如果要说嫌疑人,金美丽最有可能“涉嫌”报复。
可是金美丽今天没来,请假了。
彦霖就有些蒙圈了。
到底是谁干的?
语文老师破了一节课案,也没找到“真凶”。
“黑丫”心里明镜似的,她去看扈红。
扈红一脸的幸灾乐祸,朝她挤眼睛。
“黑丫”剜了扈红一眼,意思是你做得太过了,这样的恶作剧有点不讲究。
扈红嘴巴下沉,嘴唇下撇,意思是你现在说啥也没用了,我已经恶搞完彦霖,她遭到报复了。
徐翠翠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,时而清醒,时而糊涂。
而这段时间,窦青山也更加地忙碌起来,他不仅要搞北黄芪种植试验,还被县林业局抽调出去,与局里的几位土专家一起,给率宾县西部的几个林场“诊脉”。
哪里发生了严重的松线毛虫病,导致大面积人工松树林枯死。
父亲不在的这十几天,“黑丫”简直不堪重负,不仅要安抚母亲的情绪,还要照顾妹妹窦红英和弟弟窦英俊窦。
窦红英在林场幼儿园,明年就要上小学一年级。而窦英俊才上幼儿园小班,每天清晨,别的孩子还在睡梦中,“黑丫”就要起床帮母亲做早饭。
早饭做好后,“黑丫”要掀开妹妹弟弟的被子,把他们从热被窝里拽出来。
然后督促他们洗脸吃饭,然后她提前把妹妹和弟弟送到幼儿园,再急行军似的跑到学校。
十几天后,父亲回到朝阳林场,下了车,他就急慌慌地朝家里奔。
这些天来,他几乎吃不好睡不好,就是惦记家里的情况,他感觉家里一定会乱成一团,会堆满孩子们未洗的衣服,甚至发出刺鼻的馊味儿。
窦青山不仅惦记老婆的病情反复严重,还惦记几个小孩子的吃喝拉撒。
他甚至向上苍祈祷,离开家的这些日子,徐翠翠千万不要发病,不要给“黑丫”添乱,不然这个才8岁的女孩就太难了。
窦青山急迫地推开家门。
徐翠翠正坐在梳妆台前梳洗长头发,显然她刚刚洗完头,正用木梳一点点仔细地梳理。
“你咋才回来呢,青山,这些天你去哪了,我等你等得好苦啊!”
徐翠翠惊喜地转过头,脸上表情由喜转悲。
窦青山一边安慰妻子,一边寻找他想象中的馊了的孩子们脱下来的衣服。
可他从这屋转到那屋,再转到仓房,也没找到那堆脏衣服。
他再看屋里,看炕上,看厨房,都是井井有条,干干净净,所有的东西都置放的规规矩矩,板板正正。
窦青山心里就涌过一阵暖流,他突然眼眶一热,觉得女儿“黑丫”实在太能干了,她太不容易了。
大女儿才8岁啊,她幼小的年记,弱小的肩膀,竟然扛起了这个家,而且比自己在家时拾掇的还利索、还干净,而且一切都是那么规整……
既然家里没有杂乱无章,没有乱成一锅粥,窦青山就放心了,她简单安抚徐翠翠几句,骑上摩托车去了西山苗圃。
可是他万万没想到,晚上回来时,家里出现了令他心碎愤怒的一幕,他挥起笤帚就把徐翠翠和“黑丫”暴揍了一顿。
愤怒使得窦青山失去了理智,愤怒的他,把笤帚都打碎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