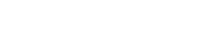漆黑的楼道内,江进酒手持一柄小型手电筒,用手指盖住灯头,从指缝中透出丝许光线照向地面。轻迈脚步,每迈出一步都要提口气,脚尖先点着地,脚掌再慢慢贴到地面上,生怕惊动楼道内的感应灯。脑袋斜歪着,左耳监听着楼下,右耳监听楼上,心里祈祷着不会有人来干扰他。
没有意外地来到四楼,乍看到401门框上贴着一排黄色的符纸,他只觉得头皮发紧。光线下移赫然照出一张大脸!一双灯泡大的眼睛凶神恶煞,他惊得心脏咯噔一下,怦怦乱跳。
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幅钟馗画像。
江进酒轻蔑一笑,心想还挺全乎,怎么不把玉皇大帝也整来呢。
可内心的嘲讽不过是在掩饰紧张,紧握钥匙的手出卖了他,大拇指甲盖里几乎没有了血色。
他缓缓的伸出手,不经意看到钟馗凶神恶煞的脸,近距离下感觉魂魄要被钟馗的两只大眼球给摄走,心慌得后退一步。
他摇头苦笑,嘲讽自己何时这般胆小。
关掉手电筒,再次伸出手,目光不自觉地瞄向钟馗。黑暗中的画像模糊不清,唯独那两只白眼仁分外清楚。他脑补了钟馗的凶相,又被吓了回去。
一鼓作气,再而衰,三而竭。他厌烦现在的安静,他希望有人给出建议,是去是留。
他两眼一抹黑地站在原地,以为过去几分钟,其实只过了几秒钟,便后悔有过厌烦安静的想法。
人在黑暗中看不见事物,听觉就会变得灵敏。
马桶冲水的声响,哗哗的水流过下水管的声响,咕咚咕咚的好像什么东西被撞翻的声音,什么东西在划拉地面的响动……夜深入静时格外清晰,却又无法辨明来源,扰的他很是心慌。尤其哐的一声楼道门关闭的声响,震得人心一颤。
江进酒不敢再耽搁,深吸一口气含在嘴里,小心翼翼的开门锁,缓缓开了一半门,挤进屋关好门,趴在门上仔细聆听,没听到什么声音,他才长长的吐了口气。
他伸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,看了一眼手表,十一点十五分。
他摇头苦笑,心想上四层楼用了十多分钟,说出去得让人笑死。
他打开手电筒,发现身处玄关,走两步便进入客厅。客厅空旷得很,一件家具摆设都没有,地面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,白色的墙壁上也粘着一层灰。墙角和屋顶的边角挂满了蜘蛛网,网里兜着灰。
他找到灯开关,却点不亮。他并不意外,去向玄关的右边。透过门上的玻璃看,里面是厨房。
他拉开门,“我去!臭死了!”
厨房的水槽上盘旋着几只苍蝇,水槽内像极了癞蛤蟆的背部,散发着下水沟里淤泥般的恶臭。
水槽下的柜门板拆掉了,下水管壁上长满了灰黑色的细毛,邻近的墙壁上长满了霉斑。蟑螂在附近肆无忌惮的游走,在白色的柜壁上留下数不清的脚印。
厨房的地面上或大或小的黑色不明物体,有的粘着苍蝇和毛毛虫的尸体,有的泛着绿色的油光,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。
他皱了皱眉头,转身走进隔壁。
这是一间次卧。
门右侧的墙角有一个落地式衣柜,柜门半开着,里面的蜘蛛网成片的交错,除了中间的隔板上有一件背心卷成一团放在角落,再无它物。
门左侧有一套桌椅,款式是七十年代后期学校教室里的木制双人课桌,单人木椅。
桌椅的对面是窗户,用蓝色的粗布窗帘遮挡着。窗帘的挂钩上粘满了蛛丝,布面上也粘满了绒毛般的尘屑。
房间的最里面摆着一张床,床头位置的床板少了两片,空隙几乎被蜘蛛网填补。透过零星的空隙可以看到下面躺着一只缺了右脚的玩具机器人,身上的尘土比周围稀薄。
江进酒认为这是一间小男孩的卧室。
见没有可疑之处,他去到对面的房间。
是主卧室,里面空无一物,连窗帘都没有,有的是更多的尘土和蜘蛛网。
但是主卧外的阳台很杂乱,大大小小的包装盒胡乱叠放,废报纸散了一地,上面还粘着一些不知名的黑色物体。
窗户边框上粘着土黄色的胶带,大部分失去黏性虚挂着,仿佛轻轻一碰便会脱落。
“只是这样?”江进酒有些失望。
他想像的鬼屋里面起码要有一幅人的半身画像,老旧的电视机,有血污的沙发,老鼠的尸体。
可这间鬼屋不过是一个尘封的世界,充满着腐朽的味道。回想白日里秦真阳说得那般严肃认真,此时他确信秦真阳想要吓唬他。
“这个世界哪来的鬼,这一定是秦老头的恶趣味。”
江进酒心中气愤,可更气的是自己当真了。然而气归气,作业还得写。
看着桌椅上寸许厚的灰尘,江进酒庆幸包里有块擦鞋布。
他本想去厨房弄湿抹布,可想起那儿的臭味就头痛。想着还没去过厕所,正好瞧上一眼。
厕所在玄关那边。
“恶心死我了!”
厕所的地面整个是黑的,酸溜溜的骚臭味夹杂着煤气般的怪味,既辣眼又刺鼻。马桶里的污垢黄中带黑,白色瓷砖砌成的墙壁上一道道棕色的印迹,不锈钢的壁挂表面上尽是点点的锈斑。洗手池里面全是锈渍,唯一干净的是钉挂在洗手台上方的木框圆镜。
其风格复古,大到可以照出半个人身,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。木头上红漆的颜色鲜艳如新,仅在下框两个对称的凹槽内有些磨损。
但是,镜子干净得太突兀了。
尽管厕所里臭气逼人,他捂着鼻子,强忍着观察镜子。
镜子是椭圆形的,木框约三指宽,顶部浮雕两朵含苞欲放的莲花,中部勾勒水纹,底部雕刻莲叶,做工十分精美。
瞧着像古装剧里面贵族千金的梳妆镜,挂在现代家居中给人的感觉十分别扭。
他取下镜子翻看背面,发现木板的中心嵌着一片约十五厘米直径的圆形青色石板,上面用油彩画了一幅观世音的座莲。只不过经过岁月的洗刷,油彩褪色,座莲如枯萎一般颜色晦暗。
江进酒看不出异常,把镜子挂回原处,顺便照上一照。
可不知怎么,他感觉有点怪怪的。
他心里认为自己的表情应该是紧着眉头,被臭味熏得难受的样子。可是镜像中的自己,同样是难受的表情,却更显阴沉。
与自己对视,镜中的目光越发冰冷,越看越觉得陌生,莫名心慌起来。他躲避镜中的目光,可是余光发现镜中的他仍然注视着自己。转眼去看,自己还是自己。他忍不住抬抬手,镜中的动作是一样的,可是眼神像在威胁自己。
他又咧嘴假笑,镜中的表情没有差别,可是眼神闪烁着,充满了狡黠与心机。
他想躲避,忽然觉得自己的目光被吸住一样无法转移,并且意识里有种眼睛正在放大,周围的光线正被黑暗吞噬的错觉。
他慌忙把手电照向自己,清楚地看到自己,怪异感就消失了。
“看样子,是光线晦暗不明引起的错觉,难怪老人说半夜不能照镜子。”
江进酒摇头苦笑,打开水龙头。
吼吼几响,出来的全是锈水,放了一会儿水才清澈。
他沾湿了抹布,抹净了桌椅。这才看到桌面上有很多铅笔和彩色水笔画的小人小物,连桌腿都不放过。尤其是右前腿的两个侧面,布满了红色的涂物,密密麻麻的,像是字又像是动物,又有可能什么都不是。
他没有在意这些,从包里拿出一根小手指粗的蜡烛点燃,接着拿出纸和笔放在桌上,开始犯愁。
江进酒爱看小说,但都是悬疑、侦探、武侠和科幻小说,没看过一本灵异类的小说。
虽然看过几部林正英的僵尸电影,可与今日毫无关系,他十分后悔同学讲鬼故事的时候走神,大伙一起听广播《xx讲鬼故事》的时候戴上耳机听音乐。
现下真是脑袋里全是碎渣,拼凑都拼不出来。
一百页的稿纸本,写了撕,撕了写,地上已有二十四个纸团。
他看了看表,马上一点钟了。可是连一个开头都没写好,心情很是郁闷。
他想发泄,于是在椅子上伸懒腰,闭紧眼睛啊啊的叫唤,感觉全身的硬块都散了才停下。然而当他放松下来时,竟然失去了意识!
约十分钟后,他的左手突然动了,搭在了桌子上,动作很不自然,就像是有人拖着他的手放在桌子上。
接着右手以同样的方式搭在桌上,然后像是被人推着背部,后仰着头坐了起来。最后脖子被人撸直,并套上了颈圈一般,脑袋微微倾斜地矗立脖子上。
整个过程他的眼睛闭着,眼珠都没动一下。
忽然他的右手抓起笔,手指却不灵活,笔掉了三次才放入两指间,生怕掉了似的紧紧地捏着,开始在纸本上划拉。
笔尖割破了纸张,他没有在意,继续他的动作。
渐渐的,他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,手指越来越灵活,最后可以写出一行规整的字迹。
一行“我”字。
这时他用左手捏起几页纸,大力的撕扯下去。在干净的页面上,开始他的书写。
他就这样一直闭着眼睛,端坐着书写。一张纸写完,便翻下一页继续写。
凌晨三点五十九分,他写下最后一个字,猛然间腰垮了,背驼了,脖子也弯了,整个人软靠在椅背上不再动弹。右手拖着笔扎在腿上,笔崩飞了他也没睁开眼睛。
时间推移,日出东方。
阳光虽然耀眼,尽被窗帘遮住。往常他该被尿意唤醒,可这会儿他睡得十分深沉。
“起床了!起床了!”
六点钟的时候,尖锐的声响从椅背上的衣服口袋中传出,把他惊醒了。
他对此表现得十分反感,满脸氲氤。
直起身揉了揉僵硬的脖子,还有左半边没有知觉的屁股,任凭手机话筒里的那个孩童声疯狂地叫喊“起床了!起床了!”。
他极尽所能地伸展筋骨,吐气的同时啊啊大叫。突然他感到胃里涌出一股恶气,赶忙捂着嘴巴冲进厕所,一阵狂呕的声音过去,想必他连胃酸水都吐得一干二净。
当他出来的时候,整个人都清醒了。不是因为大吐一场,呕吐令他更加晕沉。
他清醒的原因是被厕所里难闻的气味刺激的,此刻加入带有酒臭的呕吐物,其杀伤力堪比臭鼬的液屁。
被逼无奈他只好到厨房洗漱,就连小便也是在那里解决。
看着水龙头里流出来的黄色自来水和他的尿一样黄,他不由得发出一声长叹。
自来水在五分钟后变得清澈,他洗脸只用了五秒钟。
然后他回到卧室收拾东西,心里暗自叹息“一个月万元的好工作就这么吹了。”
苦笑着摇了摇头,把不开心的事情抛诸脑后。
可当他看到写满文字的纸张时惊得像见了鬼,站在离书桌三步远的地方想靠近又不敢,心里念叨着“我了个去!这是怎么回事!?”
他盯着桌面,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。
灰尘在朝阳的映衬中犹如金粉般飘落,很快在纸面上落了一层。光明为这个房间带来暖意,驱散人心中的阴暗。
见无甚异样,他总算鼓起勇气拿起稿纸,两行字看完,额头上的汗水涌泉般从皮肤里渗出,迅速凝聚成绿豆大的颗粒,在地球引力的牵引下滑落,直到沾湿了他的衣襟……
此刻,他已不关心纸上的内容,而是不断回忆昨夜的情形……
思来想去一切正常,唯一的疑点——怎么睡着的?
他始终想不起来。
心想就算为了壮胆喝了二锅头,可也仅仅是二两,醉也是醉两成,头没晕眼未眩,照道理讲不应该倒下,至少不会这么快才对。
可事实是睡着了,更像被人用棒子敲了一下,不痛也不痒地瞬间昏过去了。
想想好像还做了个梦,内容是什么呢?记不清,好像有个什么人,但做过些什么呢?”
突然一个惊人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“难道这是听鬼屋里的鬼写的!?”
没有意外地来到四楼,乍看到401门框上贴着一排黄色的符纸,他只觉得头皮发紧。光线下移赫然照出一张大脸!一双灯泡大的眼睛凶神恶煞,他惊得心脏咯噔一下,怦怦乱跳。
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幅钟馗画像。
江进酒轻蔑一笑,心想还挺全乎,怎么不把玉皇大帝也整来呢。
可内心的嘲讽不过是在掩饰紧张,紧握钥匙的手出卖了他,大拇指甲盖里几乎没有了血色。
他缓缓的伸出手,不经意看到钟馗凶神恶煞的脸,近距离下感觉魂魄要被钟馗的两只大眼球给摄走,心慌得后退一步。
他摇头苦笑,嘲讽自己何时这般胆小。
关掉手电筒,再次伸出手,目光不自觉地瞄向钟馗。黑暗中的画像模糊不清,唯独那两只白眼仁分外清楚。他脑补了钟馗的凶相,又被吓了回去。
一鼓作气,再而衰,三而竭。他厌烦现在的安静,他希望有人给出建议,是去是留。
他两眼一抹黑地站在原地,以为过去几分钟,其实只过了几秒钟,便后悔有过厌烦安静的想法。
人在黑暗中看不见事物,听觉就会变得灵敏。
马桶冲水的声响,哗哗的水流过下水管的声响,咕咚咕咚的好像什么东西被撞翻的声音,什么东西在划拉地面的响动……夜深入静时格外清晰,却又无法辨明来源,扰的他很是心慌。尤其哐的一声楼道门关闭的声响,震得人心一颤。
江进酒不敢再耽搁,深吸一口气含在嘴里,小心翼翼的开门锁,缓缓开了一半门,挤进屋关好门,趴在门上仔细聆听,没听到什么声音,他才长长的吐了口气。
他伸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,看了一眼手表,十一点十五分。
他摇头苦笑,心想上四层楼用了十多分钟,说出去得让人笑死。
他打开手电筒,发现身处玄关,走两步便进入客厅。客厅空旷得很,一件家具摆设都没有,地面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,白色的墙壁上也粘着一层灰。墙角和屋顶的边角挂满了蜘蛛网,网里兜着灰。
他找到灯开关,却点不亮。他并不意外,去向玄关的右边。透过门上的玻璃看,里面是厨房。
他拉开门,“我去!臭死了!”
厨房的水槽上盘旋着几只苍蝇,水槽内像极了癞蛤蟆的背部,散发着下水沟里淤泥般的恶臭。
水槽下的柜门板拆掉了,下水管壁上长满了灰黑色的细毛,邻近的墙壁上长满了霉斑。蟑螂在附近肆无忌惮的游走,在白色的柜壁上留下数不清的脚印。
厨房的地面上或大或小的黑色不明物体,有的粘着苍蝇和毛毛虫的尸体,有的泛着绿色的油光,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。
他皱了皱眉头,转身走进隔壁。
这是一间次卧。
门右侧的墙角有一个落地式衣柜,柜门半开着,里面的蜘蛛网成片的交错,除了中间的隔板上有一件背心卷成一团放在角落,再无它物。
门左侧有一套桌椅,款式是七十年代后期学校教室里的木制双人课桌,单人木椅。
桌椅的对面是窗户,用蓝色的粗布窗帘遮挡着。窗帘的挂钩上粘满了蛛丝,布面上也粘满了绒毛般的尘屑。
房间的最里面摆着一张床,床头位置的床板少了两片,空隙几乎被蜘蛛网填补。透过零星的空隙可以看到下面躺着一只缺了右脚的玩具机器人,身上的尘土比周围稀薄。
江进酒认为这是一间小男孩的卧室。
见没有可疑之处,他去到对面的房间。
是主卧室,里面空无一物,连窗帘都没有,有的是更多的尘土和蜘蛛网。
但是主卧外的阳台很杂乱,大大小小的包装盒胡乱叠放,废报纸散了一地,上面还粘着一些不知名的黑色物体。
窗户边框上粘着土黄色的胶带,大部分失去黏性虚挂着,仿佛轻轻一碰便会脱落。
“只是这样?”江进酒有些失望。
他想像的鬼屋里面起码要有一幅人的半身画像,老旧的电视机,有血污的沙发,老鼠的尸体。
可这间鬼屋不过是一个尘封的世界,充满着腐朽的味道。回想白日里秦真阳说得那般严肃认真,此时他确信秦真阳想要吓唬他。
“这个世界哪来的鬼,这一定是秦老头的恶趣味。”
江进酒心中气愤,可更气的是自己当真了。然而气归气,作业还得写。
看着桌椅上寸许厚的灰尘,江进酒庆幸包里有块擦鞋布。
他本想去厨房弄湿抹布,可想起那儿的臭味就头痛。想着还没去过厕所,正好瞧上一眼。
厕所在玄关那边。
“恶心死我了!”
厕所的地面整个是黑的,酸溜溜的骚臭味夹杂着煤气般的怪味,既辣眼又刺鼻。马桶里的污垢黄中带黑,白色瓷砖砌成的墙壁上一道道棕色的印迹,不锈钢的壁挂表面上尽是点点的锈斑。洗手池里面全是锈渍,唯一干净的是钉挂在洗手台上方的木框圆镜。
其风格复古,大到可以照出半个人身,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。木头上红漆的颜色鲜艳如新,仅在下框两个对称的凹槽内有些磨损。
但是,镜子干净得太突兀了。
尽管厕所里臭气逼人,他捂着鼻子,强忍着观察镜子。
镜子是椭圆形的,木框约三指宽,顶部浮雕两朵含苞欲放的莲花,中部勾勒水纹,底部雕刻莲叶,做工十分精美。
瞧着像古装剧里面贵族千金的梳妆镜,挂在现代家居中给人的感觉十分别扭。
他取下镜子翻看背面,发现木板的中心嵌着一片约十五厘米直径的圆形青色石板,上面用油彩画了一幅观世音的座莲。只不过经过岁月的洗刷,油彩褪色,座莲如枯萎一般颜色晦暗。
江进酒看不出异常,把镜子挂回原处,顺便照上一照。
可不知怎么,他感觉有点怪怪的。
他心里认为自己的表情应该是紧着眉头,被臭味熏得难受的样子。可是镜像中的自己,同样是难受的表情,却更显阴沉。
与自己对视,镜中的目光越发冰冷,越看越觉得陌生,莫名心慌起来。他躲避镜中的目光,可是余光发现镜中的他仍然注视着自己。转眼去看,自己还是自己。他忍不住抬抬手,镜中的动作是一样的,可是眼神像在威胁自己。
他又咧嘴假笑,镜中的表情没有差别,可是眼神闪烁着,充满了狡黠与心机。
他想躲避,忽然觉得自己的目光被吸住一样无法转移,并且意识里有种眼睛正在放大,周围的光线正被黑暗吞噬的错觉。
他慌忙把手电照向自己,清楚地看到自己,怪异感就消失了。
“看样子,是光线晦暗不明引起的错觉,难怪老人说半夜不能照镜子。”
江进酒摇头苦笑,打开水龙头。
吼吼几响,出来的全是锈水,放了一会儿水才清澈。
他沾湿了抹布,抹净了桌椅。这才看到桌面上有很多铅笔和彩色水笔画的小人小物,连桌腿都不放过。尤其是右前腿的两个侧面,布满了红色的涂物,密密麻麻的,像是字又像是动物,又有可能什么都不是。
他没有在意这些,从包里拿出一根小手指粗的蜡烛点燃,接着拿出纸和笔放在桌上,开始犯愁。
江进酒爱看小说,但都是悬疑、侦探、武侠和科幻小说,没看过一本灵异类的小说。
虽然看过几部林正英的僵尸电影,可与今日毫无关系,他十分后悔同学讲鬼故事的时候走神,大伙一起听广播《xx讲鬼故事》的时候戴上耳机听音乐。
现下真是脑袋里全是碎渣,拼凑都拼不出来。
一百页的稿纸本,写了撕,撕了写,地上已有二十四个纸团。
他看了看表,马上一点钟了。可是连一个开头都没写好,心情很是郁闷。
他想发泄,于是在椅子上伸懒腰,闭紧眼睛啊啊的叫唤,感觉全身的硬块都散了才停下。然而当他放松下来时,竟然失去了意识!
约十分钟后,他的左手突然动了,搭在了桌子上,动作很不自然,就像是有人拖着他的手放在桌子上。
接着右手以同样的方式搭在桌上,然后像是被人推着背部,后仰着头坐了起来。最后脖子被人撸直,并套上了颈圈一般,脑袋微微倾斜地矗立脖子上。
整个过程他的眼睛闭着,眼珠都没动一下。
忽然他的右手抓起笔,手指却不灵活,笔掉了三次才放入两指间,生怕掉了似的紧紧地捏着,开始在纸本上划拉。
笔尖割破了纸张,他没有在意,继续他的动作。
渐渐的,他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,手指越来越灵活,最后可以写出一行规整的字迹。
一行“我”字。
这时他用左手捏起几页纸,大力的撕扯下去。在干净的页面上,开始他的书写。
他就这样一直闭着眼睛,端坐着书写。一张纸写完,便翻下一页继续写。
凌晨三点五十九分,他写下最后一个字,猛然间腰垮了,背驼了,脖子也弯了,整个人软靠在椅背上不再动弹。右手拖着笔扎在腿上,笔崩飞了他也没睁开眼睛。
时间推移,日出东方。
阳光虽然耀眼,尽被窗帘遮住。往常他该被尿意唤醒,可这会儿他睡得十分深沉。
“起床了!起床了!”
六点钟的时候,尖锐的声响从椅背上的衣服口袋中传出,把他惊醒了。
他对此表现得十分反感,满脸氲氤。
直起身揉了揉僵硬的脖子,还有左半边没有知觉的屁股,任凭手机话筒里的那个孩童声疯狂地叫喊“起床了!起床了!”。
他极尽所能地伸展筋骨,吐气的同时啊啊大叫。突然他感到胃里涌出一股恶气,赶忙捂着嘴巴冲进厕所,一阵狂呕的声音过去,想必他连胃酸水都吐得一干二净。
当他出来的时候,整个人都清醒了。不是因为大吐一场,呕吐令他更加晕沉。
他清醒的原因是被厕所里难闻的气味刺激的,此刻加入带有酒臭的呕吐物,其杀伤力堪比臭鼬的液屁。
被逼无奈他只好到厨房洗漱,就连小便也是在那里解决。
看着水龙头里流出来的黄色自来水和他的尿一样黄,他不由得发出一声长叹。
自来水在五分钟后变得清澈,他洗脸只用了五秒钟。
然后他回到卧室收拾东西,心里暗自叹息“一个月万元的好工作就这么吹了。”
苦笑着摇了摇头,把不开心的事情抛诸脑后。
可当他看到写满文字的纸张时惊得像见了鬼,站在离书桌三步远的地方想靠近又不敢,心里念叨着“我了个去!这是怎么回事!?”
他盯着桌面,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。
灰尘在朝阳的映衬中犹如金粉般飘落,很快在纸面上落了一层。光明为这个房间带来暖意,驱散人心中的阴暗。
见无甚异样,他总算鼓起勇气拿起稿纸,两行字看完,额头上的汗水涌泉般从皮肤里渗出,迅速凝聚成绿豆大的颗粒,在地球引力的牵引下滑落,直到沾湿了他的衣襟……
此刻,他已不关心纸上的内容,而是不断回忆昨夜的情形……
思来想去一切正常,唯一的疑点——怎么睡着的?
他始终想不起来。
心想就算为了壮胆喝了二锅头,可也仅仅是二两,醉也是醉两成,头没晕眼未眩,照道理讲不应该倒下,至少不会这么快才对。
可事实是睡着了,更像被人用棒子敲了一下,不痛也不痒地瞬间昏过去了。
想想好像还做了个梦,内容是什么呢?记不清,好像有个什么人,但做过些什么呢?”
突然一个惊人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“难道这是听鬼屋里的鬼写的!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