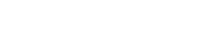第74章报官
谭安一怔,紧走几步,追问:“等一下,你们说里面传来惨叫声?”
二人被突然过来的公差吓了一跳,百姓自对公差有着天然畏惧之心,其中一人立刻就回答:“正是,我们刚才路过,离着有着一段距离,听到里面有动静。”
又一人拉了下伙伴衣角,忙说着:“我们听错了也说不定,这里挨着街道,哪就能有人行凶了?”
显然既不想得罪问话的公差,也不想平白无故招惹到事情。
谭安眼睛微亮,挥手让他们离开,他慢慢走近书肆门口,侧耳听了下。
隐隐,似是叶不悔在哭泣。
谭安心下一惊,慢慢推开了书肆的门。
一股血腥味在门打开瞬间,就冲了出来。
“里面有人受了伤!”这是谭安的第一反应,但听这哭声,他更觉得,这是叶老板出了事,不然,叶不悔不会哭爹。
他巴不得这事与苏子籍有关,但想到叶老板病情,又觉得这种可能不大,更可能是叶老板突然重病而亡。
但是这样,苏子籍此时在里面,岂不是趁虚而入,趁着这机会安抚叶不悔了?
本来不想进去的谭安,在想到这一点,一咬牙,蹑手蹑脚走了进去。
突然从内房传来声音,接着听到苏子籍的声气:“你别怕,爹既把你托付给了我,我必不会让你失望。”
一听到这话,谭安顿时如中雷殛,呆了好一阵才醒过来,偷偷往里瞧。
屋里光线很暗,苏子籍在拖着东西,第一眼看上去,天墨黑墨黑,一阵凉风袭来,谭安打了个冷噤,觉得自己眼花了。
谭安眯着眼盯过去,才看见的确是在拖个死尸,还有血从尸体慢慢流淌出来。
“这怕是凶杀!”谭安脑袋嗡的一声,心脏剧烈跳动,击鼓一样,已是再不敢往里走。
里面有着叶不悔的声音,还有苏子籍的安慰声,谭安迟疑了一下,趁里面的人没注意到自己,又慢慢转身退了出来。
直到走出书肆大门,才长出了一口气。
“苏子籍杀人了!”谭安当然不会觉得,这是叶维翰或叶不悔所杀,潜意识里,巴不得是苏子籍,所以一反应过来,心就涌出了一股喜悦。
真是苏子籍动手杀人,哪怕已是一榜案首,也再无前程可言!
不,不止毫无前程,苏子籍摊上人命官司,必会进大牢,就算看在案首份上留条命,也要革去功名,流放三千里。
到时,叶不悔无依无靠,自己再徐徐图之,还怕她不动心?
就算不动心,先得了她的身子,让叶不悔成了自己的妻子,慢慢有了孩子,不信她不回心转意。
这事几乎在脑海中过了一遍,就让谭安心中荡起无限希望。
“直接闯过去,姑且不说危险,而且还和叶不悔撕破了脸,我要立刻向上禀报,让官府抓了苏子籍,我再去安慰叶不悔!”
想到这里,谭安突然之间觉得两腿生风,奔起来简直有夜行千里之力。
“什么?苏子籍杀人了?”
谭安虽是公差,不可能轻易见到县太爷,所以当谭安回去禀报这事时,还是师爷见的他。
因前面就听说了谭安与苏子籍之间的不对付,师爷乍一听此事,就忍不住用“你疯了吧”目光打量着谭安。
“谭安,你不会是对苏子籍心存不满,不愿意去报喜信,所以故意用这种话来搪塞我吧?”
如果是这样,这小子不能留在公门当差了。
谭安忙弯腰,对师爷行礼,摆低姿态说:“师爷,您这可是冤枉我了。我承认,我对苏子籍的确有着不喜,可那不过是私怨,我身为公差,怎么可能在这种大事上欺骗您和县太爷?”
“这可是杀人大案,我说了谎,到时人一过去,不就一清二楚了?我何必撒这等一戳就穿的大谎?凭白还死里得罪人?”
这话有道理。
可谭安说得没错,难道苏子籍这个刚刚考取的秀才,真杀了人?
这可不是小事,事关刚刚考取的一榜案首,师爷不敢自己定夺,沉吟片刻,说着:“我立刻去禀报大人,李捕头。”
“师爷,您有什么吩咐?”一个铁铸一样的汉子过来。
这是负责巡捕事宜的捕头,严格说,跟谭安一样是小吏,没有品级,但在临化县里也是一号人物,就算是师爷,也相对客气。
关系一府案首,事情不小,师爷沉吟了一下,才吩咐:“你去集合巡捕,先把叶氏书肆给围了,待我去禀报大人,等着大人定夺此事。”
说着,不放心,他又叮嘱:“苏子籍是一榜案首,有着功名,要拿下要用刑都得先革了功名。”
“而且也得大人出捕票。”
县中维持治安的朝廷命官是巡检,但县令也有自己的队伍,逮捕人的权力主要掌握在郡县,如果不是县令批准就逮捕人,被发觉后要受到惩处。
“师爷放心,规矩我都懂,我这就去集合人,保准不会误了您跟大人的事。”
知道若无意外,县太爷不可能对人命大案无动于衷,李捕头立刻应声,准备带人抓捕。
至于会不会误抓好人,这事就不是李捕头负责了,只管听令行事。
“谭安,你随我一起进去见大人。”师爷对谭安说,心中暗叹,怕县令大人才好起来的心情,又要糟糕了。
果然张县令一听说此事,就大是震惊:“什么,你们是不是喝多了酒发酒疯了?一府案首杀人?”
张县令五十左右了,清癯的脸上带着倦容,本来一副稳重安详,这时都变了色,连连询问,才镇定了心神。
“这是大事,你办的非常对,先围住叶氏书肆,再派人进去调查。”
“王法不容情,谭安说得是真的话,哪怕苏子籍是新进一府案首,也不能放过,可要是此事为假……”
张县令看一眼垂手站立的谭安,冷冷说着:“我看在你们谭家的苦劳上,不入你们的罪,但你们父子都不必再留在县衙当差了。”
“请大人放心,我所说句句属实。”谭安拱手说着,汗渗了下去。
谭安一怔,紧走几步,追问:“等一下,你们说里面传来惨叫声?”
二人被突然过来的公差吓了一跳,百姓自对公差有着天然畏惧之心,其中一人立刻就回答:“正是,我们刚才路过,离着有着一段距离,听到里面有动静。”
又一人拉了下伙伴衣角,忙说着:“我们听错了也说不定,这里挨着街道,哪就能有人行凶了?”
显然既不想得罪问话的公差,也不想平白无故招惹到事情。
谭安眼睛微亮,挥手让他们离开,他慢慢走近书肆门口,侧耳听了下。
隐隐,似是叶不悔在哭泣。
谭安心下一惊,慢慢推开了书肆的门。
一股血腥味在门打开瞬间,就冲了出来。
“里面有人受了伤!”这是谭安的第一反应,但听这哭声,他更觉得,这是叶老板出了事,不然,叶不悔不会哭爹。
他巴不得这事与苏子籍有关,但想到叶老板病情,又觉得这种可能不大,更可能是叶老板突然重病而亡。
但是这样,苏子籍此时在里面,岂不是趁虚而入,趁着这机会安抚叶不悔了?
本来不想进去的谭安,在想到这一点,一咬牙,蹑手蹑脚走了进去。
突然从内房传来声音,接着听到苏子籍的声气:“你别怕,爹既把你托付给了我,我必不会让你失望。”
一听到这话,谭安顿时如中雷殛,呆了好一阵才醒过来,偷偷往里瞧。
屋里光线很暗,苏子籍在拖着东西,第一眼看上去,天墨黑墨黑,一阵凉风袭来,谭安打了个冷噤,觉得自己眼花了。
谭安眯着眼盯过去,才看见的确是在拖个死尸,还有血从尸体慢慢流淌出来。
“这怕是凶杀!”谭安脑袋嗡的一声,心脏剧烈跳动,击鼓一样,已是再不敢往里走。
里面有着叶不悔的声音,还有苏子籍的安慰声,谭安迟疑了一下,趁里面的人没注意到自己,又慢慢转身退了出来。
直到走出书肆大门,才长出了一口气。
“苏子籍杀人了!”谭安当然不会觉得,这是叶维翰或叶不悔所杀,潜意识里,巴不得是苏子籍,所以一反应过来,心就涌出了一股喜悦。
真是苏子籍动手杀人,哪怕已是一榜案首,也再无前程可言!
不,不止毫无前程,苏子籍摊上人命官司,必会进大牢,就算看在案首份上留条命,也要革去功名,流放三千里。
到时,叶不悔无依无靠,自己再徐徐图之,还怕她不动心?
就算不动心,先得了她的身子,让叶不悔成了自己的妻子,慢慢有了孩子,不信她不回心转意。
这事几乎在脑海中过了一遍,就让谭安心中荡起无限希望。
“直接闯过去,姑且不说危险,而且还和叶不悔撕破了脸,我要立刻向上禀报,让官府抓了苏子籍,我再去安慰叶不悔!”
想到这里,谭安突然之间觉得两腿生风,奔起来简直有夜行千里之力。
“什么?苏子籍杀人了?”
谭安虽是公差,不可能轻易见到县太爷,所以当谭安回去禀报这事时,还是师爷见的他。
因前面就听说了谭安与苏子籍之间的不对付,师爷乍一听此事,就忍不住用“你疯了吧”目光打量着谭安。
“谭安,你不会是对苏子籍心存不满,不愿意去报喜信,所以故意用这种话来搪塞我吧?”
如果是这样,这小子不能留在公门当差了。
谭安忙弯腰,对师爷行礼,摆低姿态说:“师爷,您这可是冤枉我了。我承认,我对苏子籍的确有着不喜,可那不过是私怨,我身为公差,怎么可能在这种大事上欺骗您和县太爷?”
“这可是杀人大案,我说了谎,到时人一过去,不就一清二楚了?我何必撒这等一戳就穿的大谎?凭白还死里得罪人?”
这话有道理。
可谭安说得没错,难道苏子籍这个刚刚考取的秀才,真杀了人?
这可不是小事,事关刚刚考取的一榜案首,师爷不敢自己定夺,沉吟片刻,说着:“我立刻去禀报大人,李捕头。”
“师爷,您有什么吩咐?”一个铁铸一样的汉子过来。
这是负责巡捕事宜的捕头,严格说,跟谭安一样是小吏,没有品级,但在临化县里也是一号人物,就算是师爷,也相对客气。
关系一府案首,事情不小,师爷沉吟了一下,才吩咐:“你去集合巡捕,先把叶氏书肆给围了,待我去禀报大人,等着大人定夺此事。”
说着,不放心,他又叮嘱:“苏子籍是一榜案首,有着功名,要拿下要用刑都得先革了功名。”
“而且也得大人出捕票。”
县中维持治安的朝廷命官是巡检,但县令也有自己的队伍,逮捕人的权力主要掌握在郡县,如果不是县令批准就逮捕人,被发觉后要受到惩处。
“师爷放心,规矩我都懂,我这就去集合人,保准不会误了您跟大人的事。”
知道若无意外,县太爷不可能对人命大案无动于衷,李捕头立刻应声,准备带人抓捕。
至于会不会误抓好人,这事就不是李捕头负责了,只管听令行事。
“谭安,你随我一起进去见大人。”师爷对谭安说,心中暗叹,怕县令大人才好起来的心情,又要糟糕了。
果然张县令一听说此事,就大是震惊:“什么,你们是不是喝多了酒发酒疯了?一府案首杀人?”
张县令五十左右了,清癯的脸上带着倦容,本来一副稳重安详,这时都变了色,连连询问,才镇定了心神。
“这是大事,你办的非常对,先围住叶氏书肆,再派人进去调查。”
“王法不容情,谭安说得是真的话,哪怕苏子籍是新进一府案首,也不能放过,可要是此事为假……”
张县令看一眼垂手站立的谭安,冷冷说着:“我看在你们谭家的苦劳上,不入你们的罪,但你们父子都不必再留在县衙当差了。”
“请大人放心,我所说句句属实。”谭安拱手说着,汗渗了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