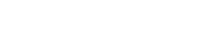第333章愿克福减寿
苏子籍却隐隐感觉到了些,回首望去,就见一个和尚,正从分开人群走出,合掌一礼。
“倒是苏公子,你本就住在居士园的一省解元,倒不必避开,若你愿意,到时可陪从迎驾。”
苏子籍有点诧异辩玄突然邀请自己,不知他在这事上扮演着什么角色,但想了下,还是答应了: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这样能够一见皇后的机会实在难得,他也有些好奇,前太子之母,究竟是什么模样。
又指着野道人与简渠:“这二人是我朋友,到我住处做客,不知可否一同放行?”
“自是可以,一炷香后,还请苏公子到殿前等候。”辩玄微笑的说着。
说完转身走了。
顶着旁人好奇的目光,这里不是说话之所,苏子籍给了赶车人车费,让其离开,带着野道人、简渠二人步行入内。
到了居士园的入口,有士兵检查了一下,就直放行。
直到远离了入口,苏子籍才问野道人:“你知不知道皇后的消息?”
野道人摇头:“曾有心查过,但没能得知一点情报。”
这事简渠竟知道一点,迟疑说着:“我昔日在西南时,倒从大帅闲聊时得知了一些消息。”
“传闻太子死后,帝后失和,但奇怪的是,虽失和,几次有妃子想当皇后,皇帝都大怒,就是宠妃,也或贬或冷落,从不心软。”
“平时怕很难听到皇后的消息,这次皇后娘娘出宫礼梵,却是难得。”
苏子籍若有所思,点了点首:“原来如此。”
说话间,他们已来到了苏子籍与叶不悔在居士园的住所,院门关着,苏子籍叩打门扉,片刻,叶不悔开门。
“不悔,你且不要忙,去换身衣裳,准备一下,一会陪我去见贵人。”其实自己还罢了,皇后可是她的奶奶,不能不见。
叶不悔才一开门,就听到了这吩咐,不由有些奇怪,就在这时,外面突传来了声音,像是鼓乐齐鸣。
“这是前面的仪仗到了。”野道人侧耳听了听。
皇后出宫,可不是小事。
就是妃子省亲,也不是立刻就直接带人出宫,而是一趟趟仪仗先到,这是给人迎驾的准备时间,何况一国之母?
等一切就绪,贵人所行的路线,已净水泼街、黄土垫道,附近都已戒严,万不会出现冲撞了凤驾的事,贵人才会在宫娥太监,以及侍卫、甲兵的保护下,出宫,前往目的地。
叶不悔没有多问究竟是要去见谁,知道时间紧迫,十分听话立刻回去准备。
就是苏子籍自己,也找出一身尚未上身的新袍换上,不求出彩但求无过。
清园寺的外面,虽不能进寺,可附近闻讯而来百姓,并没有散去,而聚拢在街道两侧,等着凤驾到来。
这样的热闹,可比状元游街难得多了,他们自然不想错过。
大郑开国后,对皇后出行仪仗,有着规定。
丹陛仪仗三十六人,丹墀仪仗五十八人,內使八人,宫女十二人。
这其中,捧着各色绣幡、扇子、伞盖的都不必说,连金交椅、金脚踏、金水盆、金水罐,都有专人抬着、捧着。
更不必说,随行的甲兵,甲胄在阳光下寒光森森。
这是除皇后仪仗外额外跟着的人——这等事情,规矩森严,但凡有增加,必是皇上的意思。
路边,所有看到仪仗而过都要跪倒,有识货的人看一眼,就倒吸一口气,低声说着:“外人说皇后娘娘受冷遇,现在看起来可不像,这般隆重,可比前朝的宠妃出行都要超过了。”
“嘘,噤声!”身旁的人见他越说越不像话,立刻低声喝止,拿本朝的皇后与前朝的后宫相比,这可是不敬。
但心里也不是不震惊,正这友人所言,从皇后出行隆重仪仗队伍就能看出,这可不像是受到冷落的皇后应有的待遇。
难道传闻有误?
苏子籍带着叶不悔来到清园寺门时,辩玄已带上百和尚在这里等候。
见他过来,还带着一个女眷,辩玄也没有说什么。
叶不悔有些紧张,见夫君表情从容,又在自己身边,紧张的心,才慢慢落回到原处。
“皇后驾到!”
一个穿着凤服,在一众宫女太监簇拥下的美妇出来时,她的心,突然不明所以地剧烈跳起来,单手按在心口,叶不悔暗向:“我也忒胆小了些,一会万不可出丑,连累了夫君。”
这样想着,努力撑起了表情,与别人一同拜下,迎接皇后到来。
“都平身吧。”皇后开口淡淡说着,在女官陪同下进了大殿,大殿中,丈八高的梵神巍然屹立,左手下垂,结“施愿印”,表示能满众生愿,右手屈臂上伸,结“施无畏印”,表示能除众生苦。
苏子籍此时已被安排,与辩玄一左一右,在旁伺候。
别人也罢了,跟随的礼部官员不知道底细,暗暗蹙眉,辩玄是和尚,又早知道风姿过人,也就罢了。
这个少年,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,戴着木冠,身穿士子衫,偏偏风姿更在其上,让人一见忘俗。
心里立刻准备弹劾。
皇后似是不觉,向银盆中盥了手,神情变得异常庄重,在公开场合,却是不能礼拜,只是福了一礼,站着静静看着梵神,喃喃祈祷:“大慈大悲之梵祖,我之一生,福寿已满,不求多增,今日上香,愿克福减寿只求一事,佑我孙儿回归宗籍,复归原位”
因离得很近,苏子籍听得清清楚楚,皇后已成女人最高位份,居然情愿减寿折福以求庇佑其孙,不禁痴了,正沉思间,皇后已默祈完,辩玄奉上檀香,苏子籍立刻醒悟过来,按照吩咐,点了火折。
皇后也不说话,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,双手插进炉里,只一颌首,又后退一步,已算是礼成。
因不能在宫外停留太久,皇后上香完就转身,缓步出去,对辩玄说:“对于庙产,朝廷自有规矩,本宫也不能许你免赋,不过可赐你水火棍一对,若有无赖地痞闹事,只管打了就是。”
水火棍是衙门里面警戒杀威的用品,长约齐眉,底端有一胫之长为红色,其他为黑色,取不容私情之意。
说完这个,下得台阶,看似随意又问着苏子籍:“你是何人?看模样,是在居士园暂住的举子?”
“是!”苏子籍忙回了。
走到大殿台阶时,皇后又问叶不悔,苏子籍抬头看一眼皇后,又回:“这是我妻叶不悔。”
皇后又看了一眼,什么都没有说,就上了辇,直接离开。
望着凤驾离开,苏子籍耳目聪惠于众人数倍,突听得御舆里面压抑不住的哽咽,似有人忍不住痛哭,又不能放出声,还有着女官惊慌又细不可闻的声音:“娘娘……”
苏子籍心下一叹,怔怔无语以对。
苏子籍却隐隐感觉到了些,回首望去,就见一个和尚,正从分开人群走出,合掌一礼。
“倒是苏公子,你本就住在居士园的一省解元,倒不必避开,若你愿意,到时可陪从迎驾。”
苏子籍有点诧异辩玄突然邀请自己,不知他在这事上扮演着什么角色,但想了下,还是答应了: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这样能够一见皇后的机会实在难得,他也有些好奇,前太子之母,究竟是什么模样。
又指着野道人与简渠:“这二人是我朋友,到我住处做客,不知可否一同放行?”
“自是可以,一炷香后,还请苏公子到殿前等候。”辩玄微笑的说着。
说完转身走了。
顶着旁人好奇的目光,这里不是说话之所,苏子籍给了赶车人车费,让其离开,带着野道人、简渠二人步行入内。
到了居士园的入口,有士兵检查了一下,就直放行。
直到远离了入口,苏子籍才问野道人:“你知不知道皇后的消息?”
野道人摇头:“曾有心查过,但没能得知一点情报。”
这事简渠竟知道一点,迟疑说着:“我昔日在西南时,倒从大帅闲聊时得知了一些消息。”
“传闻太子死后,帝后失和,但奇怪的是,虽失和,几次有妃子想当皇后,皇帝都大怒,就是宠妃,也或贬或冷落,从不心软。”
“平时怕很难听到皇后的消息,这次皇后娘娘出宫礼梵,却是难得。”
苏子籍若有所思,点了点首:“原来如此。”
说话间,他们已来到了苏子籍与叶不悔在居士园的住所,院门关着,苏子籍叩打门扉,片刻,叶不悔开门。
“不悔,你且不要忙,去换身衣裳,准备一下,一会陪我去见贵人。”其实自己还罢了,皇后可是她的奶奶,不能不见。
叶不悔才一开门,就听到了这吩咐,不由有些奇怪,就在这时,外面突传来了声音,像是鼓乐齐鸣。
“这是前面的仪仗到了。”野道人侧耳听了听。
皇后出宫,可不是小事。
就是妃子省亲,也不是立刻就直接带人出宫,而是一趟趟仪仗先到,这是给人迎驾的准备时间,何况一国之母?
等一切就绪,贵人所行的路线,已净水泼街、黄土垫道,附近都已戒严,万不会出现冲撞了凤驾的事,贵人才会在宫娥太监,以及侍卫、甲兵的保护下,出宫,前往目的地。
叶不悔没有多问究竟是要去见谁,知道时间紧迫,十分听话立刻回去准备。
就是苏子籍自己,也找出一身尚未上身的新袍换上,不求出彩但求无过。
清园寺的外面,虽不能进寺,可附近闻讯而来百姓,并没有散去,而聚拢在街道两侧,等着凤驾到来。
这样的热闹,可比状元游街难得多了,他们自然不想错过。
大郑开国后,对皇后出行仪仗,有着规定。
丹陛仪仗三十六人,丹墀仪仗五十八人,內使八人,宫女十二人。
这其中,捧着各色绣幡、扇子、伞盖的都不必说,连金交椅、金脚踏、金水盆、金水罐,都有专人抬着、捧着。
更不必说,随行的甲兵,甲胄在阳光下寒光森森。
这是除皇后仪仗外额外跟着的人——这等事情,规矩森严,但凡有增加,必是皇上的意思。
路边,所有看到仪仗而过都要跪倒,有识货的人看一眼,就倒吸一口气,低声说着:“外人说皇后娘娘受冷遇,现在看起来可不像,这般隆重,可比前朝的宠妃出行都要超过了。”
“嘘,噤声!”身旁的人见他越说越不像话,立刻低声喝止,拿本朝的皇后与前朝的后宫相比,这可是不敬。
但心里也不是不震惊,正这友人所言,从皇后出行隆重仪仗队伍就能看出,这可不像是受到冷落的皇后应有的待遇。
难道传闻有误?
苏子籍带着叶不悔来到清园寺门时,辩玄已带上百和尚在这里等候。
见他过来,还带着一个女眷,辩玄也没有说什么。
叶不悔有些紧张,见夫君表情从容,又在自己身边,紧张的心,才慢慢落回到原处。
“皇后驾到!”
一个穿着凤服,在一众宫女太监簇拥下的美妇出来时,她的心,突然不明所以地剧烈跳起来,单手按在心口,叶不悔暗向:“我也忒胆小了些,一会万不可出丑,连累了夫君。”
这样想着,努力撑起了表情,与别人一同拜下,迎接皇后到来。
“都平身吧。”皇后开口淡淡说着,在女官陪同下进了大殿,大殿中,丈八高的梵神巍然屹立,左手下垂,结“施愿印”,表示能满众生愿,右手屈臂上伸,结“施无畏印”,表示能除众生苦。
苏子籍此时已被安排,与辩玄一左一右,在旁伺候。
别人也罢了,跟随的礼部官员不知道底细,暗暗蹙眉,辩玄是和尚,又早知道风姿过人,也就罢了。
这个少年,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,戴着木冠,身穿士子衫,偏偏风姿更在其上,让人一见忘俗。
心里立刻准备弹劾。
皇后似是不觉,向银盆中盥了手,神情变得异常庄重,在公开场合,却是不能礼拜,只是福了一礼,站着静静看着梵神,喃喃祈祷:“大慈大悲之梵祖,我之一生,福寿已满,不求多增,今日上香,愿克福减寿只求一事,佑我孙儿回归宗籍,复归原位”
因离得很近,苏子籍听得清清楚楚,皇后已成女人最高位份,居然情愿减寿折福以求庇佑其孙,不禁痴了,正沉思间,皇后已默祈完,辩玄奉上檀香,苏子籍立刻醒悟过来,按照吩咐,点了火折。
皇后也不说话,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,双手插进炉里,只一颌首,又后退一步,已算是礼成。
因不能在宫外停留太久,皇后上香完就转身,缓步出去,对辩玄说:“对于庙产,朝廷自有规矩,本宫也不能许你免赋,不过可赐你水火棍一对,若有无赖地痞闹事,只管打了就是。”
水火棍是衙门里面警戒杀威的用品,长约齐眉,底端有一胫之长为红色,其他为黑色,取不容私情之意。
说完这个,下得台阶,看似随意又问着苏子籍:“你是何人?看模样,是在居士园暂住的举子?”
“是!”苏子籍忙回了。
走到大殿台阶时,皇后又问叶不悔,苏子籍抬头看一眼皇后,又回:“这是我妻叶不悔。”
皇后又看了一眼,什么都没有说,就上了辇,直接离开。
望着凤驾离开,苏子籍耳目聪惠于众人数倍,突听得御舆里面压抑不住的哽咽,似有人忍不住痛哭,又不能放出声,还有着女官惊慌又细不可闻的声音:“娘娘……”
苏子籍心下一叹,怔怔无语以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