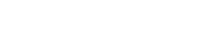清水洒在脸上,冰冷凉意,唤醒陈颜意识,睁开眼睛,豪格的脸,在眼前清晰。
她瞳孔不由紧缩,慌忙想要远离,却被人按住,大夫的手,隔着丝帕按在她手腕。
这个大夫并不是常为她看诊的大夫,是个新面孔。
大夫愁眉不展,良久,得出一个令所有人恐惧的结论。
“是天花。”
天花大名,无人不知,因为天花,八旗将士不敢在关内久待,天气稍稍回暖,便撤回关外。
陈颜大脑一片空白,她不可置信的追问道:“可我身上没有出痘。”
她见过出天花的人,全身长满红疹,幸存者身上也会留下疤痕,后世人们称康熙为“康麻子”,正是因为他幼时出花,留了疤。
“出痘之前四五日,会浑身乏力,伴随着头晕胸腹疼痛,然后会发起高烧,再然后几日,才会出痘,出痘的时候,就是最凶险的时候。”
大夫一番话,令陈颜的心跌入谷底,天花在这个时代的致死率很高,能熬过天花的寥寥无几。
“福晋目前的状况还好,不要过分担忧。”大夫安慰道。
陈颜很快接受这现实,直起身,这才发现自己正身处一顶临时搭建的帐篷下。
不远处,一群正蓝旗士兵正在卖力搭建围栏,羊皮搭在围栏,组成道道墙壁,将她圈在其中。
凡出花者,都要与健康人口隔离。
“别怕,这位大夫专治天花,在他手里活下来的病人很多。你先休息一下,行帐很快就会搭建好。”豪格也安慰陈颜。
“你不要离我这么近?”陈颜回头,看向豪格。
确诊与近距离接触过,还是有很大区别。
豪格四下看了看,此时两人身边所有护卫奴仆都被隔在围栏外,新的下人还未安排来,大夫忙着写药方,塔哲别吉正隔着围栏,和父亲哭诉,博洛台吉不断安慰她,“我的儿,别哭。”
见无人注意到他们,豪格低声道:“我小时候出过痘。”
“那你……”陈颜询问的话刚出口,就对上豪格垂下的眼眸,他就那么盯着她,坦然自若,又带着极强的侵略性。
胸口又是一痛,似乎有什么东西,要穿过她的肋骨,进入她心中。
他什么也没说,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
达哲别吉垂头丧气回来,坐在不远处,等着行帐搭起。
陈颜向她道歉,“对不起,别吉,我连累你了。”
“那个人是谁?”达哲别吉看向不远处和大夫交谈的豪格,面对这个叫出她名字的男人,小别吉目光不由困惑。
“我听阿布叫他贝勒,福晋,你认识他吗?他刚才是不是在叫你?”
“不是。”陈颜回答的干脆。
这一瞬,她的大脑出奇清醒,“他是皇上的长子,贝勒豪格,我是他的叔母,他怎么会直呼我的名字呢?”
“可是...”达哲别吉困惑道:“我并不认识这位贝勒。”
豪格走过来,在陈颜面前数步停下,他扫了一眼满眼困惑的塔哲别吉,对陈颜道:“叔母。行帐已经搭好了。”
得过天花的下人被多铎召集,送到行帐,虽然是临时搭建,但物品一应俱全,什么也不缺,就连枕头被子,都是陈颜在家中所用。
多铎派人送来了一把长命锁,是多尼满月的时候,巴特玛为他戴在脖子上的,来人还说:
“王爷说,福晋务必要以他与阿哥为念,保重身体,一家人早日团聚才好。”
陈颜摩挲银锁上繁复的花纹,心中却已经在想她若是死了,会发生什么。
多铎可以再娶,但多尼的日子或许就不好过了。
爱新觉罗家都很害怕后妈,努尔哈赤因为后妈虐待而离开家门。岳托、硕讬兄弟也是因为后妈,一个向努尔哈赤求救,一个离开家门。
他们的父亲代善甚至向努尔哈赤禀告,说硕讬投明,请求将他杀死。
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,她也曾对多尼满怀期待,想到这里,陈颜长叹口气。
也许是死过一次,陈颜对来人道:“你告诉十王,若我不幸死了,请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,务必要照顾好多尼,幼失所怙,何其可怜。”
高热比想象中来得快,天色稍暗,她身上就烫了起来,身下,还汩汩流着血,她觉得自己要变成一盘热腾腾的毛血旺。
昏沉之际,陈颜觉得床边一沉,睁开眼睛,豪格已经坐到她的床边。
她的心口又疼了,却烧得连捂住胸口的力气都没有。
这才第三天,还没到出痘的时候。
行帐搭建,有间隔顺序,他们的帐篷,离得很远。仆妇们也不知去了何处,整个行帐,只剩陈颜与豪格两人,这样的单独相处,令陈颜感到不安。
“你来做什么?”她口气生冷。
豪格垂眸,怜惜的目光中,夹杂着淡淡忧伤,透过豪格发红的眼睛,陈颜看清自己的现状。
“我让他们都出去了。”
“豪格。”陈颜气不打一处来,那些仆妇都是豫王府的人,人多口杂,多铎要是知道......
“你清醒一点。”陈颜无奈。
“这话是说给我听的,还是说给你自己听的?”豪格沉声问道。
陈颜答不上来。
世上怎么会有她这么贪心的女人,嫁了一个丈夫,却还要对另一个男人,念念不忘。
以至于造成如今困局,进退两难。都是她自己,咎由自取。
豪格继续道:“我想起很多往事,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……”
“别说了,”陈颜打断了豪格,“你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,这话说给你,也是说给我自己,我们都清醒一点。”
头沉得厉害,一用力说话,头便突突的钝痛,像是要炸开一样,陈颜闭上眼睛,眼泪顺着眼角滑落,“我不想听你说,你也不要说了,走吧。”
她必须要在豪格开口前,制止他将那番话说出口。
“女真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,相互喜爱的男女可以不顾一切的相守,世俗对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偏见。”
豪格望着陈颜,言简意赅道:“如果你愿意,等你好起来,离开他,跟我走,我会对你好的。”
她瞳孔不由紧缩,慌忙想要远离,却被人按住,大夫的手,隔着丝帕按在她手腕。
这个大夫并不是常为她看诊的大夫,是个新面孔。
大夫愁眉不展,良久,得出一个令所有人恐惧的结论。
“是天花。”
天花大名,无人不知,因为天花,八旗将士不敢在关内久待,天气稍稍回暖,便撤回关外。
陈颜大脑一片空白,她不可置信的追问道:“可我身上没有出痘。”
她见过出天花的人,全身长满红疹,幸存者身上也会留下疤痕,后世人们称康熙为“康麻子”,正是因为他幼时出花,留了疤。
“出痘之前四五日,会浑身乏力,伴随着头晕胸腹疼痛,然后会发起高烧,再然后几日,才会出痘,出痘的时候,就是最凶险的时候。”
大夫一番话,令陈颜的心跌入谷底,天花在这个时代的致死率很高,能熬过天花的寥寥无几。
“福晋目前的状况还好,不要过分担忧。”大夫安慰道。
陈颜很快接受这现实,直起身,这才发现自己正身处一顶临时搭建的帐篷下。
不远处,一群正蓝旗士兵正在卖力搭建围栏,羊皮搭在围栏,组成道道墙壁,将她圈在其中。
凡出花者,都要与健康人口隔离。
“别怕,这位大夫专治天花,在他手里活下来的病人很多。你先休息一下,行帐很快就会搭建好。”豪格也安慰陈颜。
“你不要离我这么近?”陈颜回头,看向豪格。
确诊与近距离接触过,还是有很大区别。
豪格四下看了看,此时两人身边所有护卫奴仆都被隔在围栏外,新的下人还未安排来,大夫忙着写药方,塔哲别吉正隔着围栏,和父亲哭诉,博洛台吉不断安慰她,“我的儿,别哭。”
见无人注意到他们,豪格低声道:“我小时候出过痘。”
“那你……”陈颜询问的话刚出口,就对上豪格垂下的眼眸,他就那么盯着她,坦然自若,又带着极强的侵略性。
胸口又是一痛,似乎有什么东西,要穿过她的肋骨,进入她心中。
他什么也没说,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
达哲别吉垂头丧气回来,坐在不远处,等着行帐搭起。
陈颜向她道歉,“对不起,别吉,我连累你了。”
“那个人是谁?”达哲别吉看向不远处和大夫交谈的豪格,面对这个叫出她名字的男人,小别吉目光不由困惑。
“我听阿布叫他贝勒,福晋,你认识他吗?他刚才是不是在叫你?”
“不是。”陈颜回答的干脆。
这一瞬,她的大脑出奇清醒,“他是皇上的长子,贝勒豪格,我是他的叔母,他怎么会直呼我的名字呢?”
“可是...”达哲别吉困惑道:“我并不认识这位贝勒。”
豪格走过来,在陈颜面前数步停下,他扫了一眼满眼困惑的塔哲别吉,对陈颜道:“叔母。行帐已经搭好了。”
得过天花的下人被多铎召集,送到行帐,虽然是临时搭建,但物品一应俱全,什么也不缺,就连枕头被子,都是陈颜在家中所用。
多铎派人送来了一把长命锁,是多尼满月的时候,巴特玛为他戴在脖子上的,来人还说:
“王爷说,福晋务必要以他与阿哥为念,保重身体,一家人早日团聚才好。”
陈颜摩挲银锁上繁复的花纹,心中却已经在想她若是死了,会发生什么。
多铎可以再娶,但多尼的日子或许就不好过了。
爱新觉罗家都很害怕后妈,努尔哈赤因为后妈虐待而离开家门。岳托、硕讬兄弟也是因为后妈,一个向努尔哈赤求救,一个离开家门。
他们的父亲代善甚至向努尔哈赤禀告,说硕讬投明,请求将他杀死。
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,她也曾对多尼满怀期待,想到这里,陈颜长叹口气。
也许是死过一次,陈颜对来人道:“你告诉十王,若我不幸死了,请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,务必要照顾好多尼,幼失所怙,何其可怜。”
高热比想象中来得快,天色稍暗,她身上就烫了起来,身下,还汩汩流着血,她觉得自己要变成一盘热腾腾的毛血旺。
昏沉之际,陈颜觉得床边一沉,睁开眼睛,豪格已经坐到她的床边。
她的心口又疼了,却烧得连捂住胸口的力气都没有。
这才第三天,还没到出痘的时候。
行帐搭建,有间隔顺序,他们的帐篷,离得很远。仆妇们也不知去了何处,整个行帐,只剩陈颜与豪格两人,这样的单独相处,令陈颜感到不安。
“你来做什么?”她口气生冷。
豪格垂眸,怜惜的目光中,夹杂着淡淡忧伤,透过豪格发红的眼睛,陈颜看清自己的现状。
“我让他们都出去了。”
“豪格。”陈颜气不打一处来,那些仆妇都是豫王府的人,人多口杂,多铎要是知道......
“你清醒一点。”陈颜无奈。
“这话是说给我听的,还是说给你自己听的?”豪格沉声问道。
陈颜答不上来。
世上怎么会有她这么贪心的女人,嫁了一个丈夫,却还要对另一个男人,念念不忘。
以至于造成如今困局,进退两难。都是她自己,咎由自取。
豪格继续道:“我想起很多往事,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……”
“别说了,”陈颜打断了豪格,“你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,这话说给你,也是说给我自己,我们都清醒一点。”
头沉得厉害,一用力说话,头便突突的钝痛,像是要炸开一样,陈颜闭上眼睛,眼泪顺着眼角滑落,“我不想听你说,你也不要说了,走吧。”
她必须要在豪格开口前,制止他将那番话说出口。
“女真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,相互喜爱的男女可以不顾一切的相守,世俗对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偏见。”
豪格望着陈颜,言简意赅道:“如果你愿意,等你好起来,离开他,跟我走,我会对你好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