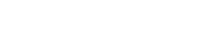凌或确实不曾明说什么威胁之语,但是他话里话外的意思,难道还不够清楚?
平阳长公主忽然抬起素手,略微摆了摆,止住了那名侍卫首领的话头。
她曼声道:“凌公子在与本宫说笑呢,你紧张什么?丢人现眼的东西。”
最后一句责骂,已然带了一丝冷然之意——那名侍卫首领当即一顿,不敢再出声了。
平阳长公主喜怒不辩、阴晴不定,平日里就十分不好伺候......即便是他这个跟随多年的护卫首领,依旧不敢丝毫犯她的忌讳。
平阳长公主似笑非笑的意有所指道:“——说来,本宫倒是不曾听闻李大人居然与‘潇湘雨下’有故。
李大人毕竟是官身,还是守卫昭歌九门的将军,不成想居然也和做着杀手买卖的贵派交情匪浅,这倒是我们昭歌中人耳目闭塞了。”
谢昭捡过话头,语态自然的道:“倒也算不上有故,只是我们家十三娘昔日曾经偶然出手救过李大人,于是我们路过昭歌城顺路拜访一番,不日便会离开。
长公主殿下想必也曾听闻,我们‘潇湘雨下’的人情可不好欠,那是要送命的,所以李大人自然要拿出接待上宾的礼仪接待我们,至于私交,还算不上。”
“十三娘”这几个字一出,在天下南北几乎有止小儿夜啼之效。
平阳长公主微微一顿,定定看向谢昭。
“哦?姑娘居然敢直呼鄙派掌门、‘十二扇刃’欧十三娘欧首座的名讳?看来身份必不简单,绝非寻常潇湘雨下弟子了。”
谢昭满不在乎的耸了耸肩。
“嗐,在下倒是没什么特别的身份,只是架不住十三娘她格外喜欢我。门中金银铜字牌子弟三千,谁人又及得上我在十三娘跟前的颜面?”
平阳长公主静了一瞬,忽然若有所思的道:
“说来,这位姑娘漏在面具外的眉眼,倒是与本宫认识的一位故人很有些相似,不知姑娘可否摘下面具,让本宫一观呢?”
谢昭笑道:“戴着面具盖因我生的太丑,天生脸上便有恶疾青斑,怕惊扰冲撞了贵人,何必惹了殿下的眼?”
平阳长公主淡笑道:“若是本宫非要看呢?”
凌或皱眉上前半步,缓缓摇头道:“殿下,还请不要为难于我们,更不要将旁人的伤痛当作玩笑戏耍,阿昭不是供人戏耍之人。”
正在此时,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,总算是终于给他们解了围。
“不知长公主殿下大驾驾临,李某有失远迎。公主上门怎未提前知会,家父也好提前在府中恭迎銮驾。”
他们齐齐松了口气,这个李遂宁,可总算是到了!
果然,李遂宁一到,平阳长公主的注意力立马便被吸引了过去。
她当即将谢昭这个看似古怪、实则出身看起来亦很低微的丑陋姑娘抛在了脑后,笑盈盈的转过身娇笑道:() ()
“遂宁,你怎么才来?本宫可等了你好半天了。”
她转过身时裙摆轻扬,一直静静伫立在轿辇旁的安氲之见状连忙脚步轻盈的上前。
他半跪在平阳长公主脚下,举止熨帖周到的替她整理华丽的裙摆。
平阳长公主含笑垂头瞥了他一眼,那一眼如无声的风情九曲回肠,她居然当着李遂宁亦丝毫不曾避讳与安氲之之间的暧昧。
凌或、韩长生相顾无言,一时不知该作何表情。
反倒是谢昭和于安安这两个姑娘家看起来更平静些——于安安是从始至终不抬头,装作一盆称职的盆栽花瓶;
而谢昭则是饶有兴趣的将视线在平阳长公主、李遂宁和那安氲之身上打转。
凌或不动声色的轻轻压了压腰间悬挂的双锏之一,那柄锏的锏鞘顺势怼在了谢昭的侧腰。
谢昭愣了愣抬头看向他,只见他微微蹙眉摇了摇头......
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——收一收你那站在天桥底下看戏的放肆表情,倒也不必这么离谱!
谢昭心虚的摸了摸下巴,低头憋笑。
这实在也不怪她嘛!
她这一年半几乎都在穷乡僻壤的小城小镇中养伤养腿,实在难以一见如此精彩的三角虐恋——啊不、应该是多角虐恋才对。
这位平阳长公主还当真是个妙人,瞧起来似乎哪一位美男都是她心尖尖上的人,不过长公主的心,恐怕是只百毒不侵的刺猬——每一根刺尖上,只怕都站着一个男人就是了。
李遂宁微微蹙眉,他似乎并不在意平阳长公主和她的男宠之间眉来眼去的情场官司,只是单纯有些看不惯她孟浪的行迹而已。
于是,他面无表情的道,“殿下,不知今日驾临九门提督府,是有什么要事?”
他没有说“李府”,而是以“九门提督府”称呼,还将重点放在了“要事”上,其中的疏离和冷淡已经昭然若揭。
——试问一位庶出长公主,有什么理由造访天宸要员九门提督的府宅?
那岂不是逾越了自己身为公主的本分?
当今天子年纪虽不大,不过手段却很是雷利风行,更是一位不愿放权、眼里不容沙的主儿。
因此纵使身为皇亲,贵胄们也更要时时自省,免得触怒天颜。
果然,平阳长公主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,她唇边娇媚的笑容微微一顿,下一刻又状若无意的放柔了声音道:
“李郎,你可真是无情,本宫来这九门提督府还能有什么要务?自然是来看望你的了。”
她的语调轻扬,仿佛棉絮搔在人的心尖儿,让韩长生听了直接暗自咋舌。
平阳长公主忽然抬起素手,略微摆了摆,止住了那名侍卫首领的话头。
她曼声道:“凌公子在与本宫说笑呢,你紧张什么?丢人现眼的东西。”
最后一句责骂,已然带了一丝冷然之意——那名侍卫首领当即一顿,不敢再出声了。
平阳长公主喜怒不辩、阴晴不定,平日里就十分不好伺候......即便是他这个跟随多年的护卫首领,依旧不敢丝毫犯她的忌讳。
平阳长公主似笑非笑的意有所指道:“——说来,本宫倒是不曾听闻李大人居然与‘潇湘雨下’有故。
李大人毕竟是官身,还是守卫昭歌九门的将军,不成想居然也和做着杀手买卖的贵派交情匪浅,这倒是我们昭歌中人耳目闭塞了。”
谢昭捡过话头,语态自然的道:“倒也算不上有故,只是我们家十三娘昔日曾经偶然出手救过李大人,于是我们路过昭歌城顺路拜访一番,不日便会离开。
长公主殿下想必也曾听闻,我们‘潇湘雨下’的人情可不好欠,那是要送命的,所以李大人自然要拿出接待上宾的礼仪接待我们,至于私交,还算不上。”
“十三娘”这几个字一出,在天下南北几乎有止小儿夜啼之效。
平阳长公主微微一顿,定定看向谢昭。
“哦?姑娘居然敢直呼鄙派掌门、‘十二扇刃’欧十三娘欧首座的名讳?看来身份必不简单,绝非寻常潇湘雨下弟子了。”
谢昭满不在乎的耸了耸肩。
“嗐,在下倒是没什么特别的身份,只是架不住十三娘她格外喜欢我。门中金银铜字牌子弟三千,谁人又及得上我在十三娘跟前的颜面?”
平阳长公主静了一瞬,忽然若有所思的道:
“说来,这位姑娘漏在面具外的眉眼,倒是与本宫认识的一位故人很有些相似,不知姑娘可否摘下面具,让本宫一观呢?”
谢昭笑道:“戴着面具盖因我生的太丑,天生脸上便有恶疾青斑,怕惊扰冲撞了贵人,何必惹了殿下的眼?”
平阳长公主淡笑道:“若是本宫非要看呢?”
凌或皱眉上前半步,缓缓摇头道:“殿下,还请不要为难于我们,更不要将旁人的伤痛当作玩笑戏耍,阿昭不是供人戏耍之人。”
正在此时,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,总算是终于给他们解了围。
“不知长公主殿下大驾驾临,李某有失远迎。公主上门怎未提前知会,家父也好提前在府中恭迎銮驾。”
他们齐齐松了口气,这个李遂宁,可总算是到了!
果然,李遂宁一到,平阳长公主的注意力立马便被吸引了过去。
她当即将谢昭这个看似古怪、实则出身看起来亦很低微的丑陋姑娘抛在了脑后,笑盈盈的转过身娇笑道:() ()
“遂宁,你怎么才来?本宫可等了你好半天了。”
她转过身时裙摆轻扬,一直静静伫立在轿辇旁的安氲之见状连忙脚步轻盈的上前。
他半跪在平阳长公主脚下,举止熨帖周到的替她整理华丽的裙摆。
平阳长公主含笑垂头瞥了他一眼,那一眼如无声的风情九曲回肠,她居然当着李遂宁亦丝毫不曾避讳与安氲之之间的暧昧。
凌或、韩长生相顾无言,一时不知该作何表情。
反倒是谢昭和于安安这两个姑娘家看起来更平静些——于安安是从始至终不抬头,装作一盆称职的盆栽花瓶;
而谢昭则是饶有兴趣的将视线在平阳长公主、李遂宁和那安氲之身上打转。
凌或不动声色的轻轻压了压腰间悬挂的双锏之一,那柄锏的锏鞘顺势怼在了谢昭的侧腰。
谢昭愣了愣抬头看向他,只见他微微蹙眉摇了摇头......
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——收一收你那站在天桥底下看戏的放肆表情,倒也不必这么离谱!
谢昭心虚的摸了摸下巴,低头憋笑。
这实在也不怪她嘛!
她这一年半几乎都在穷乡僻壤的小城小镇中养伤养腿,实在难以一见如此精彩的三角虐恋——啊不、应该是多角虐恋才对。
这位平阳长公主还当真是个妙人,瞧起来似乎哪一位美男都是她心尖尖上的人,不过长公主的心,恐怕是只百毒不侵的刺猬——每一根刺尖上,只怕都站着一个男人就是了。
李遂宁微微蹙眉,他似乎并不在意平阳长公主和她的男宠之间眉来眼去的情场官司,只是单纯有些看不惯她孟浪的行迹而已。
于是,他面无表情的道,“殿下,不知今日驾临九门提督府,是有什么要事?”
他没有说“李府”,而是以“九门提督府”称呼,还将重点放在了“要事”上,其中的疏离和冷淡已经昭然若揭。
——试问一位庶出长公主,有什么理由造访天宸要员九门提督的府宅?
那岂不是逾越了自己身为公主的本分?
当今天子年纪虽不大,不过手段却很是雷利风行,更是一位不愿放权、眼里不容沙的主儿。
因此纵使身为皇亲,贵胄们也更要时时自省,免得触怒天颜。
果然,平阳长公主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,她唇边娇媚的笑容微微一顿,下一刻又状若无意的放柔了声音道:
“李郎,你可真是无情,本宫来这九门提督府还能有什么要务?自然是来看望你的了。”
她的语调轻扬,仿佛棉絮搔在人的心尖儿,让韩长生听了直接暗自咋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