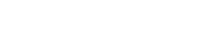西京凤翔。
元帅府的后衙中,沈珍珠手持小扇坐在火炉前,嗅到了釜内冒出香气,顾不得烫,连忙盛了汤,送往前面的议政厅。
路上,她遇到了王妃崔彩屏。
“闻着倒是好香,去,让她给我也盛一盅。”
崔彩屏正百无聊赖地倚在栏杆边,见了沈珍珠,便派婢子们去拦。如今吃穿用度不比往昔,她是真有些饿了。
沈珍珠连忙将挎篮收到身后,低头答道:“这是我给郎君炖的。”
见她不识相,崔彩屏上前,亲自伸手去拿挎篮。沈珍珠不给,崔彩屏嘴角浮起一丝笑意,转而去摸她裙里,道:“听说你腿上留了痕,给我瞧瞧。”
沈珍珠脸色剧变,连退了两步,恐惧道:“王妃你……你怎么知道?”
崔彩屏正要说话,忽听得身后动静,转头看去,恰见李俶负手走来,且脸上带着不豫之色。
“你又在欺负沈氏?!”
换作以前,李俶定不敢如此叱骂崔彩屏。彼时崔彩屏出身博陵崔氏望族,又是韩国夫人之女,地位甚高,在家中作威作福,吆五喝六,他也只能忍着。如今杨氏地位一落千丈,崔峋死在了长安,崔彩屏原本显赫的身世反而成了最受李俶嫌恶之物,自然不会有好脸色。
“妾身不敢。”
崔彩屏脾气不好,此时也只得忍着,行了一个万福之后,附在沈珠珍耳边轻声道:“真以为他心疼你?你我都是一样的处境。”
沈珍珠并不明白她这句话是何意,满心满眼只有李俶,等她走了便上前,道:“奴家给郎君炖了补汤,放了白芍、人参、肉桂,是……”
“给我吧。”
不等沈珍珠说完,李俶已伸出手,从她手里接过那个挎篮,转身走了。沈珍珠没能说出她为了凑齐补汤所需材料是如何省吃俭用,但看着他的背影也觉欢喜。
那边,李俶亲手把炖汤从挎篮中拿了出来,舀了一勺,送到了独孤琴的嘴边。
独孤琴是他新纳的妾室,禁军中一名录事参军之女。潼关失守时,她与阿爷一同随圣驾出逃,因长相分外美丽,李俶一见倾心。
她身体不太好,加上从灵武到凤翔一路跋涉,正卧病在床,没有食欲,见了李俶递过来的汤勺,偏过了头。
“喝一点吧?”李俶柔声劝道,“你这样,我好心疼。”
独孤琴摇了摇头,微微蹙眉,喃喃道:“好想吃长安丰味楼的红枣糕。”
李俶并没有因“丰味楼”三字而生气,懂得她并不知晓丰味楼背后的势力、只是单纯嘴馋,于是,他反而更喜欢她的纯粹了。
他遂握住她的手,哄道:“好,你再忍忍。很快王师就能收复长安,我带伱到龙池泛舟,到东市吃红枣糕……”
长安,禁苑。
龙首原的西南角,汉代长安的未央宫已被包围在禁苑之内,成为皇家苑囿。这里既是天子狩猎放鹰、宴饮大臣之庭院,也是禁军驻地。
薛白登上未央宫西边的雍门城楼,抬起千里镜望去,正可望到渭水、皂河之间的战场。
随着战鼓声阵阵,双方都在缓缓布阵,每走数十步都会停下来重新调整阵列,因此若纵观全局会觉得过程极慢,大半个上午过去,双方都还隔着三百余步。
薛白很有耐心,搬了一条椅子来坐着以节省体力,每次鼓声的间歇还闭上眼养养神。
“报!叛军出战了!”
“那是什么?战车?”
“是牛车。”
薛白远远望去,能看到房琯的大阵前,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战车,大概数了数,有两千辆不止。两边则是骑兵护卫着。
想必房琯行军是带了数千牛羊作为口粮的,以牛车驱为前阵,可以作为后阵的屏障,也可以冲散这边的阵列,哪怕牛被砍死了也无妨,反正得胜之后也是要宰杀了犒军的。
“这是春秋时的战法。”
此时,颜真卿也料理完别的政务匆匆赶来,走到城楼窗前望阵,道:“房公看的兵书多矣。”
“丈人是说他纸上谈兵?”薛白语气轻松地问道。
颜真卿反问道:“你可有破阵之法?”
“火攻如何?”
颜真卿抬起头看向旗帜,任风吹动他的长须,喃喃道:“唯欠东风啊。”
此时风小,吹的是西南风。
薛白不急不缓道:“风向总是会变的……传令下去,后军备柴;两翼骑兵下马歇息;再派人告诉王难得,前军缓战。”
之后,他踱了几步,招过樊牢,吩咐道:“若等不到风向,用炸药就足以惊吓牛车,你去安排。”
“喏!”
颜真卿闻言,把被风吹乱的胡须捋好,感慨道:“世情变得太快了啊。”
几年间就有了火器从无到有的变化,那么,房琯采用春秋古战法还能有多大成效呢?
再看向战场,王难得一改往日勇猛冲锋的战法,似乎是惧于房琯的牛车阵,还未战,就已经开始后撤。
兵马前行时尚且容易乱了阵型,常需调整,何况后撤?各个阵中旗帜摇摆,有的后军都还没转身,前军已经撤下来,挤在一起;有的后军撤得快了,前军失了支援,孤零零地列阵了一会,慌张后退,阵型更乱。
房琯显然也看到了长安军中的乱象,大喜,下达了进攻的命令,顿时号角声大作。可惜,牛车冲得并不算快,还是给了王难得调整的时机。
这一番折腾,时间又过去一个多时辰。到了中午,禁苑这边,薛白下令两翼的骑兵先进食、喂马,等待时机。
而在阵线最前方,王难得已被逼到了皂河边,不得不面对房琯的牛车,双方开始厮杀起来。
薛白见状,再次招过传令兵,道:“不等风势了……”
他有信心不论风向如何都能获胜,只是战果的不同而已。
“等等。”
颜真卿抬起手,感受着风拂过手背,道:“再等等,风向便会改变。”
薛白遂停止了下令。他当然相信颜真卿,虽然颜真卿是房琯的好友,但更是他的丈人。他知颜真卿忠于社稷,而他自信他是真正为大唐社稷好的一方。
房琯大帐之中,群贤林立。
帐中一角还坐着琴师董庭兰,正在操琴弹奏名曲《赤壁》,铮铮琴音,有气吞河山之慨,正适合作为此时的配音。
董庭兰很早就是房琯的门客,房琯因薛白被贬时,他落魄过一阵。后来,薛白与李隆基比戏,他为薛白配乐而得李隆基赏识,进入梨园。待李隆基出逃,他也跟在队伍当中,随着李亨的大部队到了灵武,与房琯重聚,为房琮再添风雅。
房琯久享盛名,好高谈,门下的有才之士也绝不仅有董庭兰,还有李揖、宋若思、魏少游、贾至等人,这其中有些人还与薛白颇有渊源。
宋若思乃是偃师县陆浑山庄的子弟,在全家遭难之后,把祖产出卖,到了房琯幕下,如今他得知薛白是奸臣叛逆,恍然领悟过来,当时是被薛白迫害,遂成了控诉薛白的急先锋;
魏少游虽久在朔方任官,他的家宅却位于长安城升平坊,与杜有邻是邻居,当时从雪中救回薛白的正是他的家奴。杜有邻人如其名,正因有他这个好邻居,才成了薛白的恩人;
贾至是进士出身,文名颇盛,与高适、杜甫、王维、李白交情都很好,因此对薛白的观感是不错的。如今听闻薛白是叛逆,也曾扼腕叹息。
李揖倒是与薛白无甚渊源,这人很受房琯信任,正是他提出建议,让房琯写信给长安城中的刘秩,邀请刘秩里应外合,当时房琯很高兴地说:“贼势虽炙,安能敌刘秩?”
没想到,刘秩被薛白一刀杀了,至死也没扑腾出多大的水花来。
无妨,李揖很快给房琯出了第二个主意,便是目前的牛车大阵了。此时眼看王难得左支右绌,连连后撤,房琯胜券在握,大悦,又说:“贼将虽锐,安能敌李揖之妙计?”
“轰!”
远远传来一声大响,董庭兰的琴声不由为之一顿。
帐中,有一个坐在房琯身边的宦官当即起身,尖声问道:“这是什么声音?!”
这宦官名叫邢延恩,乃是李辅国的养子,当年也曾在少阳院与李亨患难与共,因此被任为监军。天宝以来,李亨饱受李林甫、杨国忠迫害,对朝中官员并不信任,如今得了势,颇爱用当年这些不离不弃的宦官。
“监军勿惊。”李揖道:“这是贼军中的炸药,声势虽大,有牛车在前,杀伤不了我军几人……”
“牛车!”贾至脸色一变。
他虽是文人,却知牛马都是容易受惊的。
听得那轰隆大响接连,众人纷纷起身,往前线望去,只见烟气冲天而起,薛逆的叛军果然是在纵火。
魏少游抬起头一看,只见旗帜正在往北飘,不知何时,风向已变了,此时吹的是南风。
“不好了!”
说什么都晚了,原本那冲向薛逆叛军的牛车已被惊得调头乱撞,车上被点了火,风助火势,烟尘顿时迷了士卒们的眼,呛得他们眼泪直流,再被牛车一撞,当即转身就逃。
后方的士卒不知发生了什么,听得牛马嘶鸣,见到烟雾弥漫,前军后撤,当即乱作一团,迅速形成了溃败。
溃败蔓延得非常快,还不等大帐内的一众名士反应过来,十数万唐军竟是直接兵败如山倒了。
“怎么办?”
邢延恩连忙一把扯住房琯,喊叫着,声音愈发尖细。
“圣人托你大事,房相快说,眼下如何是好?!”
元帅府的后衙中,沈珍珠手持小扇坐在火炉前,嗅到了釜内冒出香气,顾不得烫,连忙盛了汤,送往前面的议政厅。
路上,她遇到了王妃崔彩屏。
“闻着倒是好香,去,让她给我也盛一盅。”
崔彩屏正百无聊赖地倚在栏杆边,见了沈珍珠,便派婢子们去拦。如今吃穿用度不比往昔,她是真有些饿了。
沈珍珠连忙将挎篮收到身后,低头答道:“这是我给郎君炖的。”
见她不识相,崔彩屏上前,亲自伸手去拿挎篮。沈珍珠不给,崔彩屏嘴角浮起一丝笑意,转而去摸她裙里,道:“听说你腿上留了痕,给我瞧瞧。”
沈珍珠脸色剧变,连退了两步,恐惧道:“王妃你……你怎么知道?”
崔彩屏正要说话,忽听得身后动静,转头看去,恰见李俶负手走来,且脸上带着不豫之色。
“你又在欺负沈氏?!”
换作以前,李俶定不敢如此叱骂崔彩屏。彼时崔彩屏出身博陵崔氏望族,又是韩国夫人之女,地位甚高,在家中作威作福,吆五喝六,他也只能忍着。如今杨氏地位一落千丈,崔峋死在了长安,崔彩屏原本显赫的身世反而成了最受李俶嫌恶之物,自然不会有好脸色。
“妾身不敢。”
崔彩屏脾气不好,此时也只得忍着,行了一个万福之后,附在沈珠珍耳边轻声道:“真以为他心疼你?你我都是一样的处境。”
沈珍珠并不明白她这句话是何意,满心满眼只有李俶,等她走了便上前,道:“奴家给郎君炖了补汤,放了白芍、人参、肉桂,是……”
“给我吧。”
不等沈珍珠说完,李俶已伸出手,从她手里接过那个挎篮,转身走了。沈珍珠没能说出她为了凑齐补汤所需材料是如何省吃俭用,但看着他的背影也觉欢喜。
那边,李俶亲手把炖汤从挎篮中拿了出来,舀了一勺,送到了独孤琴的嘴边。
独孤琴是他新纳的妾室,禁军中一名录事参军之女。潼关失守时,她与阿爷一同随圣驾出逃,因长相分外美丽,李俶一见倾心。
她身体不太好,加上从灵武到凤翔一路跋涉,正卧病在床,没有食欲,见了李俶递过来的汤勺,偏过了头。
“喝一点吧?”李俶柔声劝道,“你这样,我好心疼。”
独孤琴摇了摇头,微微蹙眉,喃喃道:“好想吃长安丰味楼的红枣糕。”
李俶并没有因“丰味楼”三字而生气,懂得她并不知晓丰味楼背后的势力、只是单纯嘴馋,于是,他反而更喜欢她的纯粹了。
他遂握住她的手,哄道:“好,你再忍忍。很快王师就能收复长安,我带伱到龙池泛舟,到东市吃红枣糕……”
长安,禁苑。
龙首原的西南角,汉代长安的未央宫已被包围在禁苑之内,成为皇家苑囿。这里既是天子狩猎放鹰、宴饮大臣之庭院,也是禁军驻地。
薛白登上未央宫西边的雍门城楼,抬起千里镜望去,正可望到渭水、皂河之间的战场。
随着战鼓声阵阵,双方都在缓缓布阵,每走数十步都会停下来重新调整阵列,因此若纵观全局会觉得过程极慢,大半个上午过去,双方都还隔着三百余步。
薛白很有耐心,搬了一条椅子来坐着以节省体力,每次鼓声的间歇还闭上眼养养神。
“报!叛军出战了!”
“那是什么?战车?”
“是牛车。”
薛白远远望去,能看到房琯的大阵前,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战车,大概数了数,有两千辆不止。两边则是骑兵护卫着。
想必房琯行军是带了数千牛羊作为口粮的,以牛车驱为前阵,可以作为后阵的屏障,也可以冲散这边的阵列,哪怕牛被砍死了也无妨,反正得胜之后也是要宰杀了犒军的。
“这是春秋时的战法。”
此时,颜真卿也料理完别的政务匆匆赶来,走到城楼窗前望阵,道:“房公看的兵书多矣。”
“丈人是说他纸上谈兵?”薛白语气轻松地问道。
颜真卿反问道:“你可有破阵之法?”
“火攻如何?”
颜真卿抬起头看向旗帜,任风吹动他的长须,喃喃道:“唯欠东风啊。”
此时风小,吹的是西南风。
薛白不急不缓道:“风向总是会变的……传令下去,后军备柴;两翼骑兵下马歇息;再派人告诉王难得,前军缓战。”
之后,他踱了几步,招过樊牢,吩咐道:“若等不到风向,用炸药就足以惊吓牛车,你去安排。”
“喏!”
颜真卿闻言,把被风吹乱的胡须捋好,感慨道:“世情变得太快了啊。”
几年间就有了火器从无到有的变化,那么,房琯采用春秋古战法还能有多大成效呢?
再看向战场,王难得一改往日勇猛冲锋的战法,似乎是惧于房琯的牛车阵,还未战,就已经开始后撤。
兵马前行时尚且容易乱了阵型,常需调整,何况后撤?各个阵中旗帜摇摆,有的后军都还没转身,前军已经撤下来,挤在一起;有的后军撤得快了,前军失了支援,孤零零地列阵了一会,慌张后退,阵型更乱。
房琯显然也看到了长安军中的乱象,大喜,下达了进攻的命令,顿时号角声大作。可惜,牛车冲得并不算快,还是给了王难得调整的时机。
这一番折腾,时间又过去一个多时辰。到了中午,禁苑这边,薛白下令两翼的骑兵先进食、喂马,等待时机。
而在阵线最前方,王难得已被逼到了皂河边,不得不面对房琯的牛车,双方开始厮杀起来。
薛白见状,再次招过传令兵,道:“不等风势了……”
他有信心不论风向如何都能获胜,只是战果的不同而已。
“等等。”
颜真卿抬起手,感受着风拂过手背,道:“再等等,风向便会改变。”
薛白遂停止了下令。他当然相信颜真卿,虽然颜真卿是房琯的好友,但更是他的丈人。他知颜真卿忠于社稷,而他自信他是真正为大唐社稷好的一方。
房琯大帐之中,群贤林立。
帐中一角还坐着琴师董庭兰,正在操琴弹奏名曲《赤壁》,铮铮琴音,有气吞河山之慨,正适合作为此时的配音。
董庭兰很早就是房琯的门客,房琯因薛白被贬时,他落魄过一阵。后来,薛白与李隆基比戏,他为薛白配乐而得李隆基赏识,进入梨园。待李隆基出逃,他也跟在队伍当中,随着李亨的大部队到了灵武,与房琯重聚,为房琮再添风雅。
房琯久享盛名,好高谈,门下的有才之士也绝不仅有董庭兰,还有李揖、宋若思、魏少游、贾至等人,这其中有些人还与薛白颇有渊源。
宋若思乃是偃师县陆浑山庄的子弟,在全家遭难之后,把祖产出卖,到了房琯幕下,如今他得知薛白是奸臣叛逆,恍然领悟过来,当时是被薛白迫害,遂成了控诉薛白的急先锋;
魏少游虽久在朔方任官,他的家宅却位于长安城升平坊,与杜有邻是邻居,当时从雪中救回薛白的正是他的家奴。杜有邻人如其名,正因有他这个好邻居,才成了薛白的恩人;
贾至是进士出身,文名颇盛,与高适、杜甫、王维、李白交情都很好,因此对薛白的观感是不错的。如今听闻薛白是叛逆,也曾扼腕叹息。
李揖倒是与薛白无甚渊源,这人很受房琯信任,正是他提出建议,让房琯写信给长安城中的刘秩,邀请刘秩里应外合,当时房琯很高兴地说:“贼势虽炙,安能敌刘秩?”
没想到,刘秩被薛白一刀杀了,至死也没扑腾出多大的水花来。
无妨,李揖很快给房琯出了第二个主意,便是目前的牛车大阵了。此时眼看王难得左支右绌,连连后撤,房琯胜券在握,大悦,又说:“贼将虽锐,安能敌李揖之妙计?”
“轰!”
远远传来一声大响,董庭兰的琴声不由为之一顿。
帐中,有一个坐在房琯身边的宦官当即起身,尖声问道:“这是什么声音?!”
这宦官名叫邢延恩,乃是李辅国的养子,当年也曾在少阳院与李亨患难与共,因此被任为监军。天宝以来,李亨饱受李林甫、杨国忠迫害,对朝中官员并不信任,如今得了势,颇爱用当年这些不离不弃的宦官。
“监军勿惊。”李揖道:“这是贼军中的炸药,声势虽大,有牛车在前,杀伤不了我军几人……”
“牛车!”贾至脸色一变。
他虽是文人,却知牛马都是容易受惊的。
听得那轰隆大响接连,众人纷纷起身,往前线望去,只见烟气冲天而起,薛逆的叛军果然是在纵火。
魏少游抬起头一看,只见旗帜正在往北飘,不知何时,风向已变了,此时吹的是南风。
“不好了!”
说什么都晚了,原本那冲向薛逆叛军的牛车已被惊得调头乱撞,车上被点了火,风助火势,烟尘顿时迷了士卒们的眼,呛得他们眼泪直流,再被牛车一撞,当即转身就逃。
后方的士卒不知发生了什么,听得牛马嘶鸣,见到烟雾弥漫,前军后撤,当即乱作一团,迅速形成了溃败。
溃败蔓延得非常快,还不等大帐内的一众名士反应过来,十数万唐军竟是直接兵败如山倒了。
“怎么办?”
邢延恩连忙一把扯住房琯,喊叫着,声音愈发尖细。
“圣人托你大事,房相快说,眼下如何是好?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