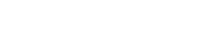益州北边三百余里,梓潼县。
此地东依梓林,西枕潼水,乃是蜀道的南大门。
十月入冬,阴雨蒙蒙,淡雾袅袅,一行人马匆匆奔至了县城北边的七曲山,因天色渐暗了,为首的骑士不得不勒住了战马。
“前方有驿馆!”
“太上皇,夜里行路危险,就在此暂歇吧?”
陈玄礼回马赶到了李隆基的马前,将他扶下了马背。一旁的卢杞抢上两步,扶住了李隆基的另一边,踉跄着走进了残败的驿馆。
剑南军兵变,他们几乎是没做任何抵挡,直接逃出行宫,一路出奔,准备去往梁州。
逃到这里,李隆基十分疲惫,问道:“叛贼不会再追来了吧?”
“这般天气,想必他们也得停下。”
在后方,张垍腿上的伤还没好,艰难地被人扶下马匹,进驿馆时却还是牵动了伤口,他疼得呲牙咧嘴,心里也蒙上了一层不安。
他原以为李隆基、李亨不论从名义还是能力,都要远强于李琮及其背后那个年轻的薛白。可自安禄山叛乱以来,李隆基的一系列昏招,终于让他意识到追随着这样一个年迈的太上皇,即使真逃到了梁州,也不会再有前途了。
抬头望去,雾蒙蒙间隐隐能看到山腰上有一座寺庙。
于是,当众人都避到了驿馆大堂,张垍便故作虚弱地拜倒在李隆基面前,道:“太上皇,臣重伤在身,恐不能随往梁州,恳请向太上皇致仕……从此,落发为僧。”
最后这句话很重要,若不表态要落发出家,李隆基必然要认为他是想投降叛贼。
张垍故意摆出凄凉怆惘的神情,眼神里满是遗憾,虽极想要继续北行偏是无可奈何,只好从此舍弃世俗,断情绝性,不再参与权势纷争。
“驸马?”
宁亲公主闻言惊诧万分,不管不顾扑到了张垍身边,道:“什么落发为僧?你怎能不与我商议一声就做此决定?!”
张垍早受够了她,这也是他想要出家的理由之一,他咳了两声,虚弱地道:“我伤重若斯,不能再拖累你与太上皇了。”
“伤重什么伤重啊?不就是腚上挨了一箭嘛。”宁亲公主嚷道,“驸马,你不能出家,我不许你出家。”
张垍不愿理她,生怕被她继续毁了自己以后的人生,小声道:“别说傻话了。”
他再次向李隆基执礼道:“恳请太上皇成全。”
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”
李隆基先是以沉郁的语气念着这诗,站起身来踱了几步,抚着他花白的长须,缓缓道:“朕已七十岁了,犹有壮志。你才多大岁数,怎可如此消沉?”
张垍惭愧,泣道:“臣一介凡夫俗子,岂可与太上皇相比?”
这话说得很好听,换成旁人致仕,李隆基就放过他了,可张垍不同。
“起来。”李隆基上前,以他苍老却还算有力的臂膀扶起他,道:“打起精神来,朕还需要你作证,证明薛白冒充朕的孙子,他是假的,是逆贼。这些是你亲口与朕说过的话,朕要你向长安百官证明!”
张垍愣了愣,应道:“不错,薛白是薛锈收养的一个贱奴,从出身就是逆贼,此事许多人都可作证。”
“还有谁可作证?”
张垍不由转头看了一眼宁亲公主,心想当年那宅院里收容的薛锈家人,全都被这恶毒女人杀了,又还有几个证人?
他略略犹豫,只好道:“咸宜公主与驸马杨洄可作证。”
李隆基摇了摇头,道:“朕需要伱。”
张垍嚅了嚅嘴,道:“臣愿为太上皇效死……”
话音未了,他因失血过多加上连日奔波,终于晕倒在地上,仿佛只有佛法能够救他。
李隆基见状,心中不悦,一种众叛亲离的感受更加强烈了。
天色更黑下来,夜里,李隆基辗转反侧,迷迷糊糊中似听到了远处有什么声音在响。
“三郎……三郎……”
他恍然间想起了在长安宫阙时杨玉环对他的呼喊,可脑子才清醒了些,他便想到杨玉环此时也许正与薛白在翻云覆雨,心中便添了许多苦楚,遂再也睡不着。
于是他翻身而起,推门而出,只见陈玄礼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外守着,盔甲也没卸,但似乎睡着了。
“圣人。”听到动静,陈玄礼惊醒过来,无意中用了以前的称谓唤李隆基。
“朕仿佛听到有人在唤‘三郎’,出来看看。”
陈玄礼倾耳听了一会,应道:“那是山寺上的铃在响,响的是‘当啷’‘当啷’。”
李隆基怆然道:“雨夜闻铃,教人肠断啊。”
“陛下忧思过重了。”
“可有琴?”
“臣这就去找。”
陈玄礼匆匆让人寻乐器,可这趟被赶出行宫时慌慌张张的,根本没带笨重的琴与鼓。唯从一個随行的伶人处找到一支短笛。
“朕欲新作一曲,便名为《雨淋铃》吧。”
李隆基接过短笛,用袖子擦着,竟不嫌弃是旁人用过的,放到嘴边吹起来。
笛声悠扬宛转,如泣如诉,仿佛诉说着他无人能懂的哀叹……
“果然在这里!”
忽然,一声大喝从驿馆外传来,笛声戛然而止。
李隆基放下手中的短笛,惊诧地看向陈玄礼,嚅了嚅嘴,终于问道:“驿馆被包围了?”
陈玄礼对此并不知情,发愣了好一会,才答道:“臣……臣睡着了,臣有罪。”
“驸马!”
宁亲公主慌慌张张地跑到驿馆大堂,奔到了张垍的身旁,不停地推着他,道:“怎么办?叛贼追过来了。”
张垍本打算一直晕下去,无奈被她推得太晃了,只好睁开眼制止了她,喃喃道:“别推了。”
“怎么办啊?叛贼已经包围过来了。”
张垍本就在思忖此事,他认为自己身份特殊,最有资格证明薛白就是皇孙李倩。换言之,他是能够给予薛白正统名义的关键人物,薛白定然是不会杀他的。
可之前彼此有过节,再加上他驸马的身份,助薛白谋篡之后,不可能得到重用,等薛白稳固了地位,还有可能杀他灭口。
眼下被包围在这驿馆之中,能自保的办法却少。张垍思来想去,还是决定出家,既表示自己宁可出世也不愿降贼的名节,又能与李唐皇室分割干净,往后以僧人的身份做选择,也有更多余地。
“帮我剃度。”张垍道,“我要落发为僧。”
“那我怎么办?”宁亲公主大怒道。
“你也出家吧。”张垍劝道,“莫忘了,那宅院里的遗孤全是你害死的。”
宁亲公主吓得脸色惨白,连忙招过随从道:“快,给我与驸马剃度!”
驿馆客房数量有限,卢杞也是歇在大堂之上,见了张垍夫妇如此行径,很是不齿,大骂道:“张垍,你世受国恩,社稷危难之际不挺身而出,遁入佛门躲避吗?”
“我为国征战,身负重伤,无力动弹。今太上皇危难,我欲以死殉节,可我若死,谁来揭薛白之阴谋?”
“你!”
卢杞嫉妒张垍有那丹书铁契一般的免死符,恨得只咬牙。
他却不能放弃已到手的宰相之位,连忙要去拥着太上皇逃,然而,驿馆大门处轰然大响,禁军们退了进来。
反贼已经冲到了门外。
“太上皇为奸臣裹挟,我等要救出太上皇,护送回长安!”
随着这声大喝,一群剑南兵迈过大门,出现在了卢杞的视线中。他知道他们所说的“奸臣”就是自己,不由打了个冷颤。
“住手!”
正在此时,严武带着姜亥、田神功、田神玉等几名将领赶到,大喝道:“不许伤了太上皇!”
接着,他对列阵守在院中的禁军们问道:“圣人在长安翘首以盼,等着与太上皇父子相聚,你等举刀拦着,是要造反吗?!”
他气势慑人,吓得一些禁军想要放下手中的刀。
正在此时,李隆基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“朕看你才要造反!”
众人转头看去,只见李隆基在陈玄礼的护卫下已赶到了,站在后方的安全之处,道:“朕没有被奸臣挟持,因不肖子为奸人蛊惑,朕为维护宗社,方以耄耋之躯辗转南幸。严武,现在朕亲自谕降,你幡然悔悟尤未晚也。”
严武顶着压力,道:“太上皇是被奸臣劫持了才这般说。”
“朕还没糊涂!”李隆基道:“没有奸臣,你立即给朕退下。”
姜亥认为这般对峙下去没完没了,当即抬手一指卢杞,喝道:“那就是奸臣,斩杀了他!”
这就是清君侧了,等见了血,他看李隆基还敢不敢硬气。
话罢,姜亥第一个动手,举刀上前便去斩卢杞。
“拦住此贼!”陈玄礼喝令禁军去拦。
双方就此当着李隆基的面厮杀起来。
原本激愤的剑南军士卒追到这里,怒气已消了不少,当着太上皇的面前谋逆便有些犹豫,许多人不敢动手。包括严武也是沉着一张脸,没有下任何命令。
反倒是郭千仞,位卑职小,无知无畏,敢向卢杞冲杀过去。
陈玄礼见状连忙护着李隆向后撤。
卢杞也是胆战心惊,有心要逃。他第一次与薛白交手,惹了杀身之祸便是求他阿爷把他送出长安。今日再次遇到危险,脑子里首先想到的还是找他阿爷。
可他阿爷已经死了。
“你们不能杀我!”卢杞惊呼道,“我阿爷在洛阳死节,人人敬佩!你们不能杀我!”
此地东依梓林,西枕潼水,乃是蜀道的南大门。
十月入冬,阴雨蒙蒙,淡雾袅袅,一行人马匆匆奔至了县城北边的七曲山,因天色渐暗了,为首的骑士不得不勒住了战马。
“前方有驿馆!”
“太上皇,夜里行路危险,就在此暂歇吧?”
陈玄礼回马赶到了李隆基的马前,将他扶下了马背。一旁的卢杞抢上两步,扶住了李隆基的另一边,踉跄着走进了残败的驿馆。
剑南军兵变,他们几乎是没做任何抵挡,直接逃出行宫,一路出奔,准备去往梁州。
逃到这里,李隆基十分疲惫,问道:“叛贼不会再追来了吧?”
“这般天气,想必他们也得停下。”
在后方,张垍腿上的伤还没好,艰难地被人扶下马匹,进驿馆时却还是牵动了伤口,他疼得呲牙咧嘴,心里也蒙上了一层不安。
他原以为李隆基、李亨不论从名义还是能力,都要远强于李琮及其背后那个年轻的薛白。可自安禄山叛乱以来,李隆基的一系列昏招,终于让他意识到追随着这样一个年迈的太上皇,即使真逃到了梁州,也不会再有前途了。
抬头望去,雾蒙蒙间隐隐能看到山腰上有一座寺庙。
于是,当众人都避到了驿馆大堂,张垍便故作虚弱地拜倒在李隆基面前,道:“太上皇,臣重伤在身,恐不能随往梁州,恳请向太上皇致仕……从此,落发为僧。”
最后这句话很重要,若不表态要落发出家,李隆基必然要认为他是想投降叛贼。
张垍故意摆出凄凉怆惘的神情,眼神里满是遗憾,虽极想要继续北行偏是无可奈何,只好从此舍弃世俗,断情绝性,不再参与权势纷争。
“驸马?”
宁亲公主闻言惊诧万分,不管不顾扑到了张垍身边,道:“什么落发为僧?你怎能不与我商议一声就做此决定?!”
张垍早受够了她,这也是他想要出家的理由之一,他咳了两声,虚弱地道:“我伤重若斯,不能再拖累你与太上皇了。”
“伤重什么伤重啊?不就是腚上挨了一箭嘛。”宁亲公主嚷道,“驸马,你不能出家,我不许你出家。”
张垍不愿理她,生怕被她继续毁了自己以后的人生,小声道:“别说傻话了。”
他再次向李隆基执礼道:“恳请太上皇成全。”
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”
李隆基先是以沉郁的语气念着这诗,站起身来踱了几步,抚着他花白的长须,缓缓道:“朕已七十岁了,犹有壮志。你才多大岁数,怎可如此消沉?”
张垍惭愧,泣道:“臣一介凡夫俗子,岂可与太上皇相比?”
这话说得很好听,换成旁人致仕,李隆基就放过他了,可张垍不同。
“起来。”李隆基上前,以他苍老却还算有力的臂膀扶起他,道:“打起精神来,朕还需要你作证,证明薛白冒充朕的孙子,他是假的,是逆贼。这些是你亲口与朕说过的话,朕要你向长安百官证明!”
张垍愣了愣,应道:“不错,薛白是薛锈收养的一个贱奴,从出身就是逆贼,此事许多人都可作证。”
“还有谁可作证?”
张垍不由转头看了一眼宁亲公主,心想当年那宅院里收容的薛锈家人,全都被这恶毒女人杀了,又还有几个证人?
他略略犹豫,只好道:“咸宜公主与驸马杨洄可作证。”
李隆基摇了摇头,道:“朕需要伱。”
张垍嚅了嚅嘴,道:“臣愿为太上皇效死……”
话音未了,他因失血过多加上连日奔波,终于晕倒在地上,仿佛只有佛法能够救他。
李隆基见状,心中不悦,一种众叛亲离的感受更加强烈了。
天色更黑下来,夜里,李隆基辗转反侧,迷迷糊糊中似听到了远处有什么声音在响。
“三郎……三郎……”
他恍然间想起了在长安宫阙时杨玉环对他的呼喊,可脑子才清醒了些,他便想到杨玉环此时也许正与薛白在翻云覆雨,心中便添了许多苦楚,遂再也睡不着。
于是他翻身而起,推门而出,只见陈玄礼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外守着,盔甲也没卸,但似乎睡着了。
“圣人。”听到动静,陈玄礼惊醒过来,无意中用了以前的称谓唤李隆基。
“朕仿佛听到有人在唤‘三郎’,出来看看。”
陈玄礼倾耳听了一会,应道:“那是山寺上的铃在响,响的是‘当啷’‘当啷’。”
李隆基怆然道:“雨夜闻铃,教人肠断啊。”
“陛下忧思过重了。”
“可有琴?”
“臣这就去找。”
陈玄礼匆匆让人寻乐器,可这趟被赶出行宫时慌慌张张的,根本没带笨重的琴与鼓。唯从一個随行的伶人处找到一支短笛。
“朕欲新作一曲,便名为《雨淋铃》吧。”
李隆基接过短笛,用袖子擦着,竟不嫌弃是旁人用过的,放到嘴边吹起来。
笛声悠扬宛转,如泣如诉,仿佛诉说着他无人能懂的哀叹……
“果然在这里!”
忽然,一声大喝从驿馆外传来,笛声戛然而止。
李隆基放下手中的短笛,惊诧地看向陈玄礼,嚅了嚅嘴,终于问道:“驿馆被包围了?”
陈玄礼对此并不知情,发愣了好一会,才答道:“臣……臣睡着了,臣有罪。”
“驸马!”
宁亲公主慌慌张张地跑到驿馆大堂,奔到了张垍的身旁,不停地推着他,道:“怎么办?叛贼追过来了。”
张垍本打算一直晕下去,无奈被她推得太晃了,只好睁开眼制止了她,喃喃道:“别推了。”
“怎么办啊?叛贼已经包围过来了。”
张垍本就在思忖此事,他认为自己身份特殊,最有资格证明薛白就是皇孙李倩。换言之,他是能够给予薛白正统名义的关键人物,薛白定然是不会杀他的。
可之前彼此有过节,再加上他驸马的身份,助薛白谋篡之后,不可能得到重用,等薛白稳固了地位,还有可能杀他灭口。
眼下被包围在这驿馆之中,能自保的办法却少。张垍思来想去,还是决定出家,既表示自己宁可出世也不愿降贼的名节,又能与李唐皇室分割干净,往后以僧人的身份做选择,也有更多余地。
“帮我剃度。”张垍道,“我要落发为僧。”
“那我怎么办?”宁亲公主大怒道。
“你也出家吧。”张垍劝道,“莫忘了,那宅院里的遗孤全是你害死的。”
宁亲公主吓得脸色惨白,连忙招过随从道:“快,给我与驸马剃度!”
驿馆客房数量有限,卢杞也是歇在大堂之上,见了张垍夫妇如此行径,很是不齿,大骂道:“张垍,你世受国恩,社稷危难之际不挺身而出,遁入佛门躲避吗?”
“我为国征战,身负重伤,无力动弹。今太上皇危难,我欲以死殉节,可我若死,谁来揭薛白之阴谋?”
“你!”
卢杞嫉妒张垍有那丹书铁契一般的免死符,恨得只咬牙。
他却不能放弃已到手的宰相之位,连忙要去拥着太上皇逃,然而,驿馆大门处轰然大响,禁军们退了进来。
反贼已经冲到了门外。
“太上皇为奸臣裹挟,我等要救出太上皇,护送回长安!”
随着这声大喝,一群剑南兵迈过大门,出现在了卢杞的视线中。他知道他们所说的“奸臣”就是自己,不由打了个冷颤。
“住手!”
正在此时,严武带着姜亥、田神功、田神玉等几名将领赶到,大喝道:“不许伤了太上皇!”
接着,他对列阵守在院中的禁军们问道:“圣人在长安翘首以盼,等着与太上皇父子相聚,你等举刀拦着,是要造反吗?!”
他气势慑人,吓得一些禁军想要放下手中的刀。
正在此时,李隆基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“朕看你才要造反!”
众人转头看去,只见李隆基在陈玄礼的护卫下已赶到了,站在后方的安全之处,道:“朕没有被奸臣挟持,因不肖子为奸人蛊惑,朕为维护宗社,方以耄耋之躯辗转南幸。严武,现在朕亲自谕降,你幡然悔悟尤未晚也。”
严武顶着压力,道:“太上皇是被奸臣劫持了才这般说。”
“朕还没糊涂!”李隆基道:“没有奸臣,你立即给朕退下。”
姜亥认为这般对峙下去没完没了,当即抬手一指卢杞,喝道:“那就是奸臣,斩杀了他!”
这就是清君侧了,等见了血,他看李隆基还敢不敢硬气。
话罢,姜亥第一个动手,举刀上前便去斩卢杞。
“拦住此贼!”陈玄礼喝令禁军去拦。
双方就此当着李隆基的面厮杀起来。
原本激愤的剑南军士卒追到这里,怒气已消了不少,当着太上皇的面前谋逆便有些犹豫,许多人不敢动手。包括严武也是沉着一张脸,没有下任何命令。
反倒是郭千仞,位卑职小,无知无畏,敢向卢杞冲杀过去。
陈玄礼见状连忙护着李隆向后撤。
卢杞也是胆战心惊,有心要逃。他第一次与薛白交手,惹了杀身之祸便是求他阿爷把他送出长安。今日再次遇到危险,脑子里首先想到的还是找他阿爷。
可他阿爷已经死了。
“你们不能杀我!”卢杞惊呼道,“我阿爷在洛阳死节,人人敬佩!你们不能杀我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