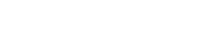太子妻妾有太子妃、良娣、宝林三个等级,杜二娘杜妗是良娣,秩正三品。
今年正月,太子妃韦氏因韦坚案被迫与太子和离。对此,杜妗喜于自己有了成为太子妃的可能,同时却也心中惴惴。
这日才送了太子出门,婢女曲水便匆匆赶来禀报道:“大娘让人拿了信物来,称出了天大之事。”
杜妗知道长姐自从嫁了柳勣之后嫁妆几乎卖尽,唯有一枚玉佩还在,接过一看,连忙吩咐带人进来。
“天大之事?”她已预感到不好,泛起一阵颤栗,自语道:“如履薄冰,终究掉进了冰窟窿。”
她调整了情绪,赶到偏厅,正见一个小郎君正襟危坐于蒲团之上,气度沉稳。
可当他回过头来,杜妗却察觉到了一种被审视之感。
她不由微微蹙眉,问道:“敢问小郎子是何人?”
“郎子”是对英俊少年的美称,加了个“小”字则是她下意识对于被薛白审视的反抗。
“薛白,受了杜家恩惠。”薛白单刀直入道:“柳郎婿状告杜家‘妄称图谶,交构东宫,指斥乘舆’,京兆府已拿了令尊。此事有人在背后操纵,我们已找到证据,想呈给太子。”
杜妗脸色瞬间一变,但迅速冷静下来。
“太子不在,可否先将证据给妾身看看?”
薛白拿出那张状纸的草稿。
曲水正要上前,杜妗已俯身到薛白面前接过,一片白腻映入他眼帘。
隐约的香气飘过,她拿着那稿纸在对面的薄团上缓缓跪坐下来,仔细看了,招过曲水,低声道:“速让人去请太子回来。”
其后,她才向薛白问了详细的经过,薛白遂从他昏迷失忆在杜家当书童开始事无巨细地说了。
杜妗听过,拍了拍心口,露出庆幸之态,道:“薛郎子为杜家奔走,妾身今日微寒无以为报,往后必重谢。”
薛白却缓缓道:“我虽然失了记忆,但却知道自己既然被人打得奄奄一息,一定是之前得罪了什么人。今日过来时外面有人盯梢,这些人也许会查到我失忆之前的事,给太子带来麻烦?”
杜妗目光一凝,听出了他的言下之意。说是怕给太子带来麻烦,实则是想要太子的庇护。
她语气有了些细微的变化,道:“你若惹了什么麻烦可以直说,妾身能帮的,绝不推托。”
薛白道:“但我真不记得了。”
杜妗略感不快。
薛白又道:“青岚说我脖后有烙印、腿上有勒伤,该是官奴。”
“看你模样,可是富贵人家被籍没为奴的?”
“想不起,但有可能。”
杜妗愿意还这个人情,但太子如今的处境并不好。在不知道薛白身上的麻烦是大是小的情况下,贸然答应庇护难免有风险。
于是她再一次仔仔细细地打量了薛白一会,思忖着这个人值不值得帮。
最后,杜妗点了点头,道:“好吧,妾身会保你无事。”
薛白稍稍松了一口气,问道:“我可否见见太子?”
“太子事忙,不便见你。”杜妗眼波一转,道:“你若有事,与妾身说也是一样的,东宫绝不会亏待你。”
薛白看向她,看到了一种很熟悉的眼神,马上明白过来——同样是为东宫做事,她希望他是帮她做事。
可见,她与太子虽是夫妻,两人之间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。
薛白不动声色,道:“我听说了年初发生的韦坚案,一直在想,如果这回太子再次放弃身边的人,对人心也不利吧?”
他俨然已有成为了太子良娣幕下谋士之态,站在杜妗的角度考虑问题。
青岚见此情形惊诧不已,自杜家救了薛白至今只有五日,他却日日都能显露出更多奇异来,可见城府极深。
杜妗却极需要这样的人,不由面露微笑,道:“你放心,我不是韦妃,且我们有了能证明杜家清白的证据,此案简单,翻案已不难。”
这一笑风情万种,她确实是容易让男人不顾一切的美人。
接着,她轻声补了一句,道:“当然,你这句话,我也会委婉地让太子知道。储君乃国本,不说威望,最后一点体面无论如何也得保住。”
薛白深以为然地点点头,问道:“二娘打算如何用这证据?”
他也称她“二娘”,而非“杜良娣”,杜妗反而再次会心一笑,道:“太子须与几位侍讲商议,拿出最妥善的办法。”
这就不是薛白能涉及的问题了,他遂问道:“是谁在背后捣鬼?”
杜妗微微冷笑道:“除了当朝右相李林甫还能有谁?”
薛白没有说话,静待下文。
“李林甫小字哥奴,因他生性狠狡,面无和气、精神刚戾,如同一只索斗之鸡,朝中国士呼他为‘索斗鸡’,他当年极力支持立寿王为储君,自认为在册立太子一事中无功劳,遂想动摇东宫。年初的韦坚案便是他大兴冤狱之结果……”
杜妗一张嘴颇为厉害,把李林甫骂了個体无完肤,最后总结道:“此人嫉贤妒能、为祸天下,着实是个大奸臣。”
薛白听的时候十分认真。
他正襟危坐,偶尔手指会不自觉地摆出了虚握的姿势抖动两下,像是捏着一支铅粉笔在记录。
杜妗目光看去,推测他以前有听人说话时拿笔记下来的习惯。
说过了李林甫,薛白沉吟片刻,又问道:“朝中可有杨国忠?”
杜妗想了想,摇头道:“未听闻过此人。”
“是杨贵妃之兄。”
“杨贵妃只有三个姐姐,一个夭折的兄弟。”杜妗道:“倒是今岁跑来一个不着调的堂兄,是个唾壶。”
“唾壶?”
“说来却有桩故事,若非如此,妾身还不知此人。”杜妗道:“此人名杨钊,嗜酒赌博,为亲族鄙夷,只好到西川谋生计。似乎在去岁吧?从西川回了长安,到处送礼,巴结上了李林甫。”
说到这里,她嘴角向下一撇,挥了挥袖子,才继续说起来。
“某日,李林甫从皇城出来,一口老痰含在嘴里无处可吐,杨钊正伴在左右,忙将嘴张开,请李林甫吐在他嘴里,遂有‘唾壶’之称。一个索斗鸡、一个唾壶,同流合污。”
青岚在旁啊,不由十分嫌弃地“咦”了一声,一阵恶寒。
薛白也是半晌无语。
心中暗想,看来这杨钊便是杨国忠了,如今还未发迹。
杜妗问道:“你为何打听此人?可是柳勣与他有所来往?”
薛白不动声色,反问道:“二娘为何如此认为?”
“柳勣任左骁卫兵曹,杨钊任右骁卫兵曹,又皆是恨不能淹死在酒池里的性子,有所往来也正常。”杜妗道:“你是说……柳勣就是被杨钊引见给吉温的?大姐与你说的?”
薛白昨夜与杜媗谈了良久,杜媗却并不了解朝中这些人物,只说柳勣回家后从不说这些。
相比而言,杜妗久浸权谋,思路果然要灵活得多。
薛白听她一说,瞬间收获不少,沉吟着开口道:“此案的关……”
正在此时,曲水匆匆跑回来,禀道:“太子回来了。”
“这么快?”杜妗有些讶异。
“奴婢派去的人不过刚出门,想来太子该是听到了什么消息才赶回来的。”
杜妗点点头,起身去迎,同时向薛白交代道:“待妾身见过太子再迎大姐、五郎,你们且在此等候,莫随意走动。”
~~
杜妗待人宽厚,还不忘命人给薛白、青岚备了午膳。
但午膳过后,薛白在太子别院一直等了很久,却不见她回来。
直到一个身披红色圆领窄袖袍衫的中年男人小跑过来。
这人四十岁左右年纪,躬腰塌背,相貌奇丑,双目鼓胀,前额突起,龅牙盘曲,脸上无须……应该是一个宦官。
“某乃东宫宦官李静忠,敢问可是薛郎君当面?”
李静忠声音奇怪,应该是没到变声期就被阉掉了。
薛白忙行了一礼,道:“正是。”
李静忠上前,凑到薛白身前,低声道:“李林甫派人来了,明为探望,实为搜查。”
不等薛白反应,他手一抬,又道:“快请薛郎君这边来。”
他们出了偏厅,不敢再往前院走,而是顺着长廊快步赶到后院。
到了长廊尽头,李静忠低头一看,见薛白、青岚的鞋还留在前院,连忙招过几个小宦官吩咐把靴子脱下给他们换上。
薛白没说什么,向前院看了一眼。
青岚则扁了扁嘴才穿上那小宦官的靴子,因靴子大了些,走起路来便磕磕绊绊。
穿过两进院子,只见后罩院侧门边已套好了一辆运泔水的马车,上面放着一口大缸,车边还站着好几个奴仆装扮的汉子,个个身材高大骁健。
李静忠带着他们到了缸边,道:“外间有人盯着,还请伱们暂时委屈一下。此缸干净的,厨房的大水缸。”
薛白不情愿进去,道:“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杜家清白。”
“是啊。”李静忠急道:“但这证据从何而来的?总不能是太子派人去拿的,得交由旁人来洗清杜家的冤枉,得藏好了你们,才好用这证据啊。”
“杜家姐弟呢?”
“自也该送过去,可眼下哪能顾得上呀?”
“外面有人盯着,万一被拿到反而解释不清。”薛白道:“是否对方故意逼我们露破绽?”
李静忠急得跺脚,道:“放心,已安排妥了……快走吧,太子处境可大不妙啊。”
他是真的着急,伸手将青岚扶进缸里,又来扶薛白。
薛白一进去,青岚见他凑得这么近,连忙闭上眼、捂住胸前。
“蹲下。”李静忠不停催促,亲手拿起一块圆木盖板压下来。
如此,两个人蹲在缸里便有些挤了。
黑暗罩下来,只剩木盖板间细缝里透着些许微光。
李静忠在外面吩咐道:“快,把泔水桶搬上去,盖板绑一绑,莫掉了……外面如何了?”
“可以走了。”
大缸晃了几下,之后轱辘声响起。
车上颠得厉害,薛白与青岚不时被碰撞在一起,初时青岚很慌张,渐渐才习惯了。
过了很久很久马车才停下。
大缸被人抬起,晃动得厉害,青岚“呀”的一声,彻底倒在薛白怀里。
薛白顾不得她,伸手去推那盖板,盖板却已被麻绳绑住了。
透过缝隙,他见到所处的却是荒郊野岭。
“放我们出去!”
外面毫无动静,大缸在晃动了几下之后被摆在地上,响起了细微的沙沙声。
仿佛雨打在屋檐上。
薛白一瞬间想到了之前的许多细节,心知这是要活埋他与青岚。
他猛撞上方的盖板,才撞开一点,马上有大汉踩了上来。
眼看推不出去,他连忙大喊道:“杀了我们对你主人毫无好处,只会给他招祸。”
“沙沙沙沙……”
“你们想要什么我都能给!信我,我与这世上旁人都不同,可以给你们很多东西!你们要钱吗?想要多少钱尽管开口。”
青岚也已明白发生了什么,双手顶着盖板,哭喊道:“求求你们了……放了我们吧……求你们了……”
混乱中,她忽然感到薛白的双手在摸自己的脚,更加害怕,尖叫不已。
“啊!别这样……”
然而沙沙声始终不停,且越来越小。
终于,盖板与缸口的缝隙里再没有了光亮,也再听不到外面的动静。
只剩下彻底的黑暗。
今年正月,太子妃韦氏因韦坚案被迫与太子和离。对此,杜妗喜于自己有了成为太子妃的可能,同时却也心中惴惴。
这日才送了太子出门,婢女曲水便匆匆赶来禀报道:“大娘让人拿了信物来,称出了天大之事。”
杜妗知道长姐自从嫁了柳勣之后嫁妆几乎卖尽,唯有一枚玉佩还在,接过一看,连忙吩咐带人进来。
“天大之事?”她已预感到不好,泛起一阵颤栗,自语道:“如履薄冰,终究掉进了冰窟窿。”
她调整了情绪,赶到偏厅,正见一个小郎君正襟危坐于蒲团之上,气度沉稳。
可当他回过头来,杜妗却察觉到了一种被审视之感。
她不由微微蹙眉,问道:“敢问小郎子是何人?”
“郎子”是对英俊少年的美称,加了个“小”字则是她下意识对于被薛白审视的反抗。
“薛白,受了杜家恩惠。”薛白单刀直入道:“柳郎婿状告杜家‘妄称图谶,交构东宫,指斥乘舆’,京兆府已拿了令尊。此事有人在背后操纵,我们已找到证据,想呈给太子。”
杜妗脸色瞬间一变,但迅速冷静下来。
“太子不在,可否先将证据给妾身看看?”
薛白拿出那张状纸的草稿。
曲水正要上前,杜妗已俯身到薛白面前接过,一片白腻映入他眼帘。
隐约的香气飘过,她拿着那稿纸在对面的薄团上缓缓跪坐下来,仔细看了,招过曲水,低声道:“速让人去请太子回来。”
其后,她才向薛白问了详细的经过,薛白遂从他昏迷失忆在杜家当书童开始事无巨细地说了。
杜妗听过,拍了拍心口,露出庆幸之态,道:“薛郎子为杜家奔走,妾身今日微寒无以为报,往后必重谢。”
薛白却缓缓道:“我虽然失了记忆,但却知道自己既然被人打得奄奄一息,一定是之前得罪了什么人。今日过来时外面有人盯梢,这些人也许会查到我失忆之前的事,给太子带来麻烦?”
杜妗目光一凝,听出了他的言下之意。说是怕给太子带来麻烦,实则是想要太子的庇护。
她语气有了些细微的变化,道:“你若惹了什么麻烦可以直说,妾身能帮的,绝不推托。”
薛白道:“但我真不记得了。”
杜妗略感不快。
薛白又道:“青岚说我脖后有烙印、腿上有勒伤,该是官奴。”
“看你模样,可是富贵人家被籍没为奴的?”
“想不起,但有可能。”
杜妗愿意还这个人情,但太子如今的处境并不好。在不知道薛白身上的麻烦是大是小的情况下,贸然答应庇护难免有风险。
于是她再一次仔仔细细地打量了薛白一会,思忖着这个人值不值得帮。
最后,杜妗点了点头,道:“好吧,妾身会保你无事。”
薛白稍稍松了一口气,问道:“我可否见见太子?”
“太子事忙,不便见你。”杜妗眼波一转,道:“你若有事,与妾身说也是一样的,东宫绝不会亏待你。”
薛白看向她,看到了一种很熟悉的眼神,马上明白过来——同样是为东宫做事,她希望他是帮她做事。
可见,她与太子虽是夫妻,两人之间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。
薛白不动声色,道:“我听说了年初发生的韦坚案,一直在想,如果这回太子再次放弃身边的人,对人心也不利吧?”
他俨然已有成为了太子良娣幕下谋士之态,站在杜妗的角度考虑问题。
青岚见此情形惊诧不已,自杜家救了薛白至今只有五日,他却日日都能显露出更多奇异来,可见城府极深。
杜妗却极需要这样的人,不由面露微笑,道:“你放心,我不是韦妃,且我们有了能证明杜家清白的证据,此案简单,翻案已不难。”
这一笑风情万种,她确实是容易让男人不顾一切的美人。
接着,她轻声补了一句,道:“当然,你这句话,我也会委婉地让太子知道。储君乃国本,不说威望,最后一点体面无论如何也得保住。”
薛白深以为然地点点头,问道:“二娘打算如何用这证据?”
他也称她“二娘”,而非“杜良娣”,杜妗反而再次会心一笑,道:“太子须与几位侍讲商议,拿出最妥善的办法。”
这就不是薛白能涉及的问题了,他遂问道:“是谁在背后捣鬼?”
杜妗微微冷笑道:“除了当朝右相李林甫还能有谁?”
薛白没有说话,静待下文。
“李林甫小字哥奴,因他生性狠狡,面无和气、精神刚戾,如同一只索斗之鸡,朝中国士呼他为‘索斗鸡’,他当年极力支持立寿王为储君,自认为在册立太子一事中无功劳,遂想动摇东宫。年初的韦坚案便是他大兴冤狱之结果……”
杜妗一张嘴颇为厉害,把李林甫骂了個体无完肤,最后总结道:“此人嫉贤妒能、为祸天下,着实是个大奸臣。”
薛白听的时候十分认真。
他正襟危坐,偶尔手指会不自觉地摆出了虚握的姿势抖动两下,像是捏着一支铅粉笔在记录。
杜妗目光看去,推测他以前有听人说话时拿笔记下来的习惯。
说过了李林甫,薛白沉吟片刻,又问道:“朝中可有杨国忠?”
杜妗想了想,摇头道:“未听闻过此人。”
“是杨贵妃之兄。”
“杨贵妃只有三个姐姐,一个夭折的兄弟。”杜妗道:“倒是今岁跑来一个不着调的堂兄,是个唾壶。”
“唾壶?”
“说来却有桩故事,若非如此,妾身还不知此人。”杜妗道:“此人名杨钊,嗜酒赌博,为亲族鄙夷,只好到西川谋生计。似乎在去岁吧?从西川回了长安,到处送礼,巴结上了李林甫。”
说到这里,她嘴角向下一撇,挥了挥袖子,才继续说起来。
“某日,李林甫从皇城出来,一口老痰含在嘴里无处可吐,杨钊正伴在左右,忙将嘴张开,请李林甫吐在他嘴里,遂有‘唾壶’之称。一个索斗鸡、一个唾壶,同流合污。”
青岚在旁啊,不由十分嫌弃地“咦”了一声,一阵恶寒。
薛白也是半晌无语。
心中暗想,看来这杨钊便是杨国忠了,如今还未发迹。
杜妗问道:“你为何打听此人?可是柳勣与他有所来往?”
薛白不动声色,反问道:“二娘为何如此认为?”
“柳勣任左骁卫兵曹,杨钊任右骁卫兵曹,又皆是恨不能淹死在酒池里的性子,有所往来也正常。”杜妗道:“你是说……柳勣就是被杨钊引见给吉温的?大姐与你说的?”
薛白昨夜与杜媗谈了良久,杜媗却并不了解朝中这些人物,只说柳勣回家后从不说这些。
相比而言,杜妗久浸权谋,思路果然要灵活得多。
薛白听她一说,瞬间收获不少,沉吟着开口道:“此案的关……”
正在此时,曲水匆匆跑回来,禀道:“太子回来了。”
“这么快?”杜妗有些讶异。
“奴婢派去的人不过刚出门,想来太子该是听到了什么消息才赶回来的。”
杜妗点点头,起身去迎,同时向薛白交代道:“待妾身见过太子再迎大姐、五郎,你们且在此等候,莫随意走动。”
~~
杜妗待人宽厚,还不忘命人给薛白、青岚备了午膳。
但午膳过后,薛白在太子别院一直等了很久,却不见她回来。
直到一个身披红色圆领窄袖袍衫的中年男人小跑过来。
这人四十岁左右年纪,躬腰塌背,相貌奇丑,双目鼓胀,前额突起,龅牙盘曲,脸上无须……应该是一个宦官。
“某乃东宫宦官李静忠,敢问可是薛郎君当面?”
李静忠声音奇怪,应该是没到变声期就被阉掉了。
薛白忙行了一礼,道:“正是。”
李静忠上前,凑到薛白身前,低声道:“李林甫派人来了,明为探望,实为搜查。”
不等薛白反应,他手一抬,又道:“快请薛郎君这边来。”
他们出了偏厅,不敢再往前院走,而是顺着长廊快步赶到后院。
到了长廊尽头,李静忠低头一看,见薛白、青岚的鞋还留在前院,连忙招过几个小宦官吩咐把靴子脱下给他们换上。
薛白没说什么,向前院看了一眼。
青岚则扁了扁嘴才穿上那小宦官的靴子,因靴子大了些,走起路来便磕磕绊绊。
穿过两进院子,只见后罩院侧门边已套好了一辆运泔水的马车,上面放着一口大缸,车边还站着好几个奴仆装扮的汉子,个个身材高大骁健。
李静忠带着他们到了缸边,道:“外间有人盯着,还请伱们暂时委屈一下。此缸干净的,厨房的大水缸。”
薛白不情愿进去,道:“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杜家清白。”
“是啊。”李静忠急道:“但这证据从何而来的?总不能是太子派人去拿的,得交由旁人来洗清杜家的冤枉,得藏好了你们,才好用这证据啊。”
“杜家姐弟呢?”
“自也该送过去,可眼下哪能顾得上呀?”
“外面有人盯着,万一被拿到反而解释不清。”薛白道:“是否对方故意逼我们露破绽?”
李静忠急得跺脚,道:“放心,已安排妥了……快走吧,太子处境可大不妙啊。”
他是真的着急,伸手将青岚扶进缸里,又来扶薛白。
薛白一进去,青岚见他凑得这么近,连忙闭上眼、捂住胸前。
“蹲下。”李静忠不停催促,亲手拿起一块圆木盖板压下来。
如此,两个人蹲在缸里便有些挤了。
黑暗罩下来,只剩木盖板间细缝里透着些许微光。
李静忠在外面吩咐道:“快,把泔水桶搬上去,盖板绑一绑,莫掉了……外面如何了?”
“可以走了。”
大缸晃了几下,之后轱辘声响起。
车上颠得厉害,薛白与青岚不时被碰撞在一起,初时青岚很慌张,渐渐才习惯了。
过了很久很久马车才停下。
大缸被人抬起,晃动得厉害,青岚“呀”的一声,彻底倒在薛白怀里。
薛白顾不得她,伸手去推那盖板,盖板却已被麻绳绑住了。
透过缝隙,他见到所处的却是荒郊野岭。
“放我们出去!”
外面毫无动静,大缸在晃动了几下之后被摆在地上,响起了细微的沙沙声。
仿佛雨打在屋檐上。
薛白一瞬间想到了之前的许多细节,心知这是要活埋他与青岚。
他猛撞上方的盖板,才撞开一点,马上有大汉踩了上来。
眼看推不出去,他连忙大喊道:“杀了我们对你主人毫无好处,只会给他招祸。”
“沙沙沙沙……”
“你们想要什么我都能给!信我,我与这世上旁人都不同,可以给你们很多东西!你们要钱吗?想要多少钱尽管开口。”
青岚也已明白发生了什么,双手顶着盖板,哭喊道:“求求你们了……放了我们吧……求你们了……”
混乱中,她忽然感到薛白的双手在摸自己的脚,更加害怕,尖叫不已。
“啊!别这样……”
然而沙沙声始终不停,且越来越小。
终于,盖板与缸口的缝隙里再没有了光亮,也再听不到外面的动静。
只剩下彻底的黑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