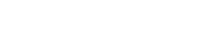偃月堂中温暖如春,熏香比前堂淡些,气味却更为宜人。
李林甫身穿紫色官袍,外披大氅,正在给老子的画像上香,口中低声道:“大圣祖玄元皇帝保佑。”
他时年六十又三,乃李唐宗室出身,其曾祖父乃李渊之堂弟、长平郡王李叔良。
将三柱香线插在神案前,他转过头来。
那张脸峻拔有威,双眉直竖如剑,两颊有些络腮,胡须粗硬、根根刚劲,双瞳相距较短,有好斗之气。
他像一座陡峭巍峨的山,给人一种“险峻”之感。
“见过右相。”
薛白行了叉手礼,感受到润奴正在身后盯着自己。
除此之外,李林甫身边还有两名胡袍婢女护卫在侧,可见其小心,却不知这样一个小心的人物为何召自己到这偃月堂?
“朝中多骂老夫奸相而同情李亨,你投效老夫,可担心于名声有碍?”
“我只知李亨要坑杀我,而右相愿保我。”
“谁说要保你?你若敢有欺瞒,老夫教你不得好死。”
“不敢。”
“李亨暗中积蓄,本相早有猜测。”李林甫眼中精芒一绽,道:“你说能助本相废太子,若只有这些,可无用。”
薛白正要开口,只觉脖颈一凉,润奴竟是已持着匕首架在他颈上。
“我便可为证据。”他不慌不忙道:“我遭活埋而不死,李亨得知,必遣人来灭口。右相只需拿住他派来杀我的死士,便可顺藤摸瓜。”
“竖子未免将自己看得太重!”
“那右相不妨押我到圣人面前,但我虽愿出面指证李亨,圣人却未必会信啊。”
李林甫沉吟起来。
薛白还待开口,屋外忽响起一声“阿郎”,有女婢匆匆进来,低声向李林甫禀报了几句。
李林甫听罢,向薛白问道:“柳勣之供状草稿,是你交给李亨?”
“正是。”
“且先看李亨是如何利用此证据。”
说罢,李林甫抬手稍稍一指,示意那女婢向薛白解释。
“今日正是大理寺、御史台、京兆府台三司会审杜有邻案。”
李林甫淡淡道:“本相特意不去,还命吉温候在府中,便是想看看李亨有多少小手段。”
薛白却知道,他是临时起意不去的,微微笑道:“是,右相已有了更致命的办法,不需要在这点小案上费神。”
“等着吧。”
李林甫闭目小憩。
~~
大理寺到右相府一路还在静街。
唯有左右骁卫骑卒奔走传递消息。
终于,一封信报交到相府管事苍璧手中,正要送往偃月堂。
“啊!”
忽然听得一声骇人的惨叫,苍璧停下脚步看去,见那是皎奴还在问话,连忙又继续埋头奔走。
前堂,皎奴已从杜五郎胳膊上割下一块薄皮来,问道:“薄吗?”
青岚目光看去,只见杜五郎胳膊有一片发红,渗了细细的血,与小擦伤一般浅,再看那块薄皮,确实是薄如蝉翼。
皎奴道:“今日若阿郎不满意,我就把你们三个的皮这般一块块地割下来。”
青岚连忙道:“我说的都是真的啊!”
皎奴却反手又给了杜五郎一巴掌。
“别哭了蠢狗,你方才不是忠肝义胆吗?”
“……”
苍璧则已赶到了偃月堂,稍稍平复了喘息。
“阿郎,信报到了。”
“也给这竖子听听。”
“喏。”
苍璧摊开信纸,一句句报起来。
“京兆尹韩朝宗不等右相、吉温到场,执意开审,左相陈希烈、御史中丞杨慎矜都没拦住他。”
“王鉷、罗希奭等三司官员纷纷举证,证明柳勣、杜有邻心怀不轨、图谋扶立东宫……”
薛白目光看去,观察到李林甫微不可察地叹息了一声。
李亨已经切断了与杜家之间的关系,在圣人面前表现得很乖巧。那这案子再如何,已动不了其太子之位。
此案还在争的不过是“人心”,若能牵扯更广、杀更多人,朝臣便知李林甫势焰正盛;而李亨需要偷偷摸摸保住一批人,才能不使更多人心寒。
~~
其后,消息一封又一封,几乎就没断过。
“阿郎,韩朝宗提出了新的证据,乃是柳勣的供状草稿,逼着柳勣翻了供。业已将三司会审的结果递到宫中,请圣人裁断。”
李林甫淡淡道:“他可有说,如何得到的这草稿?”
“称长安县尉颜真卿昨日至柳宅探查,于废墟之下拾得,有许多不良人亲眼看到他俯身拾起并摊开纸团。”
李林甫面露讥笑,开口道:“薛白,此事你如何看待?”
薛白道:“纸团也许真是颜县尉拾到的,但是谁放回那里的便不得而知了。”
“你很了得。”李林甫拍掌赞道:“你找到的证据,你为杜家翻了案,了得,了得。”
“我做了蠢事,让右相见笑了。”
“可惜啊!”李林甫高声长叹道:“可惜伱千辛万苦找的证据,送到了一个窝囊废手里,他连亲自将证据拿出来的勇气都没有,终日躲躲藏藏、鬼鬼祟祟。天下岂能交到这样一个无能的储君手里?!”
话到最后,声色俱厉。
苍璧惶恐不已,躬身应道:“阿郎,韩朝宗如此行事,不过因阿郎不在。是否尽快将这小子送去,指证东宫?”
“李亨并未派我烧毁证据,我去作证只能算栽赃,动不了他。”薛白道:“韦坚一案‘交构边镇大将’的大罪尚且未能废了他,这次更不行。唯有拿到李亨蓄养死士的证据,而我愿为右相当这个饵。”
话到这里,他已意识到自己说的多了、急了,李林甫是何等聪慧之人,岂需他这般解释?
果然,李林甫只以冷峻的眼神扫了他一眼,淡淡道:“少年郎心急,且待着,看看即便翻了案又能如何?”
~~
与李林甫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等消息并不舒服。
到了午间,相府有奴婢把酒菜送到偃月堂,并当着李林甫的面每道菜都小试了一口,他才放心享用。
薛白则站在那等着,看着窗外的景色,陷入了沉思。
待李林甫用过饭,在俏婢们的服侍下漱口、净手,当薛白不存在一般。
终于。
“阿郎,判了。”
“念。”
“柳勣、杜有邻等要犯,杖一百,家小流徙岭南,一应受柳勣行贿之官员,严惩不怠!”
“哈哈!翻了案还是死!翻案?”李林甫大笑,那双狠厉的眼神中似有了笑意,道:“莫说杖一百,杖三十便足以杖死他们。”
他又证明了一件事——他想要谁死,谁就得死,怎么挣扎都没用。
待到笑够了,他才问道:“你可知圣人为何如此?”
薛白方才一直在思考,开口便打算道一句“我愚钝,请右相赐教”,如此,李林甫便可装腔作势说上几句霸气之语。
但话到嘴边,他忽又想到,与其在李林甫面前藏拙,倒不如露拙。
“圣人也心知杜家是冤枉的。但圣人却要天下臣工看清楚,凡是想要投靠李亨以求飞黄腾达之人,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“竖子!”
“圣人要的太子是一個毫无助力的孤家寡人,等所有人都不敢亲近太子,太子也就没有了威胁。”
“够了!”李林甫拍案叱道:“妄自揣度圣意,你好大胆!”
薛白面无惧色,应道:“我若不大胆,如何敢助右相废太子?还有,右相已越来越难对付李亨了,因为李亨已经被右相羞辱了太多次,反而成了圣人眼里最软弱、最不具威胁的儿子!二月春风似剪刀,他的把柄都被右相剪了,他成了个毫无破绽的木头,最弱、也是最无懈可击,今日之后李亨的太子之位稳如泰山,皆拜右相所赐!”
“掌嘴!掌嘴!”
李林甫勃然大怒,倏地起身,指着薛白怒吼道。
一直以来,他自诩洞悉圣意,却唯独在这件事上太急了,此时才意识到薛白所言之理。
“右相千辛万苦,李亨却只要把支持他的人全部抛弃就能够得到圣人的满意。只有我的办法能拿到他的把柄……”
润奴一用力踹在薛白膝弯处。
薛白硬挨了,却不肯跪。
润奴大恼,脚下一勾,以胳膊卡住他的脖子,硬是将他摁倒在地。她力气极大,又有巧劲,翻身制住他,一手持匕挟他,一手抬起便要掌他嘴。
“右相!我正是在大缸中看明白了此间道理,翻案无用,李亨更是护不了任何人,故我欲投效右相,并不想在右相面前假装,愿助右相废了他!”
“那好。”
李林甫眼中精光闪烁,起身,踱步沉吟着,终于回过头道:“给你一个为老夫办事的机会,你来拿住李亨之罪证,真正能废了他的罪证。”
“好!”薛白道:“留下我,能成为梗在他喉咙里的刺,他早晚要拔刺。”
“你不错,明事理,率直坦荡,恩怨分明。”
润奴重重哼了一声,松开手,放薛白起身。
李林甫沉声道:“老夫于偃月堂中为国定计除奸,无往不利。今日定下除李亨之大计,你莫要辜负。”
薛白此时才知为何他让自己到偃月堂密谈,而不是屏退左右,竟只是为了讨个彩头。
“定不负右相重托!”
“你能体悟圣意,可是官宦子弟出身?”
“我于雪地昏死之后,前事一概忘了,此事千真万确。”
“也好,便当前事大梦一场,往后重新来过。”
“是。”薛白应了,却又拱手道:“我还有一事相请,恳请右相放过杜家。”
“莫得寸进尺。”
薛白道:“今李亨为自保而舍杜良娣。若杜家下场惨烈,世人只会认为是右相逼迫,衬得李亨可怜可叹。反之,若右相放过杜家,世人则只会道右相宽仁,李亨无情可笑。”
李林甫不悦道:“本相不需世人风评!”
“薛白与杜家皆不过蝼蚁而已,而蝼蚁有蝼蚁的用途!我听闻松赞干布向太宗皇帝求娶文成公主,太宗曾给他出过一个难题,要他将丝线穿过有九曲孔道的明珠,松赞干布百思不得其法,最后让蝼蚁系着丝线爬过九曲孔道,完成了穿线。”
薛白说着,再次郑重其事地行了个叉手礼,道:“薛白与杜家,愿为右相穿线。”
“还从未有人为本相办事是先提条件的。”李林甫字字森然,缓缓道:“你若想求死,本不该浪费本相时间。”
“我还是那六个字,恩必报、债必偿。”
“本相不是你能说服的。”
“却不知右相可有杜二娘消息?”
李林甫一听,脸色便沉下来。
他手底下有些人确实显得废物了。
“李亨好手段,看似无权无势,却事事瞒人耳目。”薛白道:“右相若能保了杜家,或可利用杜家找到杜二娘,从而找到其蓄养死士的证据。”
“你能做到?”
“五日之内,必给右相一个满意的结果。”
李林甫身穿紫色官袍,外披大氅,正在给老子的画像上香,口中低声道:“大圣祖玄元皇帝保佑。”
他时年六十又三,乃李唐宗室出身,其曾祖父乃李渊之堂弟、长平郡王李叔良。
将三柱香线插在神案前,他转过头来。
那张脸峻拔有威,双眉直竖如剑,两颊有些络腮,胡须粗硬、根根刚劲,双瞳相距较短,有好斗之气。
他像一座陡峭巍峨的山,给人一种“险峻”之感。
“见过右相。”
薛白行了叉手礼,感受到润奴正在身后盯着自己。
除此之外,李林甫身边还有两名胡袍婢女护卫在侧,可见其小心,却不知这样一个小心的人物为何召自己到这偃月堂?
“朝中多骂老夫奸相而同情李亨,你投效老夫,可担心于名声有碍?”
“我只知李亨要坑杀我,而右相愿保我。”
“谁说要保你?你若敢有欺瞒,老夫教你不得好死。”
“不敢。”
“李亨暗中积蓄,本相早有猜测。”李林甫眼中精芒一绽,道:“你说能助本相废太子,若只有这些,可无用。”
薛白正要开口,只觉脖颈一凉,润奴竟是已持着匕首架在他颈上。
“我便可为证据。”他不慌不忙道:“我遭活埋而不死,李亨得知,必遣人来灭口。右相只需拿住他派来杀我的死士,便可顺藤摸瓜。”
“竖子未免将自己看得太重!”
“那右相不妨押我到圣人面前,但我虽愿出面指证李亨,圣人却未必会信啊。”
李林甫沉吟起来。
薛白还待开口,屋外忽响起一声“阿郎”,有女婢匆匆进来,低声向李林甫禀报了几句。
李林甫听罢,向薛白问道:“柳勣之供状草稿,是你交给李亨?”
“正是。”
“且先看李亨是如何利用此证据。”
说罢,李林甫抬手稍稍一指,示意那女婢向薛白解释。
“今日正是大理寺、御史台、京兆府台三司会审杜有邻案。”
李林甫淡淡道:“本相特意不去,还命吉温候在府中,便是想看看李亨有多少小手段。”
薛白却知道,他是临时起意不去的,微微笑道:“是,右相已有了更致命的办法,不需要在这点小案上费神。”
“等着吧。”
李林甫闭目小憩。
~~
大理寺到右相府一路还在静街。
唯有左右骁卫骑卒奔走传递消息。
终于,一封信报交到相府管事苍璧手中,正要送往偃月堂。
“啊!”
忽然听得一声骇人的惨叫,苍璧停下脚步看去,见那是皎奴还在问话,连忙又继续埋头奔走。
前堂,皎奴已从杜五郎胳膊上割下一块薄皮来,问道:“薄吗?”
青岚目光看去,只见杜五郎胳膊有一片发红,渗了细细的血,与小擦伤一般浅,再看那块薄皮,确实是薄如蝉翼。
皎奴道:“今日若阿郎不满意,我就把你们三个的皮这般一块块地割下来。”
青岚连忙道:“我说的都是真的啊!”
皎奴却反手又给了杜五郎一巴掌。
“别哭了蠢狗,你方才不是忠肝义胆吗?”
“……”
苍璧则已赶到了偃月堂,稍稍平复了喘息。
“阿郎,信报到了。”
“也给这竖子听听。”
“喏。”
苍璧摊开信纸,一句句报起来。
“京兆尹韩朝宗不等右相、吉温到场,执意开审,左相陈希烈、御史中丞杨慎矜都没拦住他。”
“王鉷、罗希奭等三司官员纷纷举证,证明柳勣、杜有邻心怀不轨、图谋扶立东宫……”
薛白目光看去,观察到李林甫微不可察地叹息了一声。
李亨已经切断了与杜家之间的关系,在圣人面前表现得很乖巧。那这案子再如何,已动不了其太子之位。
此案还在争的不过是“人心”,若能牵扯更广、杀更多人,朝臣便知李林甫势焰正盛;而李亨需要偷偷摸摸保住一批人,才能不使更多人心寒。
~~
其后,消息一封又一封,几乎就没断过。
“阿郎,韩朝宗提出了新的证据,乃是柳勣的供状草稿,逼着柳勣翻了供。业已将三司会审的结果递到宫中,请圣人裁断。”
李林甫淡淡道:“他可有说,如何得到的这草稿?”
“称长安县尉颜真卿昨日至柳宅探查,于废墟之下拾得,有许多不良人亲眼看到他俯身拾起并摊开纸团。”
李林甫面露讥笑,开口道:“薛白,此事你如何看待?”
薛白道:“纸团也许真是颜县尉拾到的,但是谁放回那里的便不得而知了。”
“你很了得。”李林甫拍掌赞道:“你找到的证据,你为杜家翻了案,了得,了得。”
“我做了蠢事,让右相见笑了。”
“可惜啊!”李林甫高声长叹道:“可惜伱千辛万苦找的证据,送到了一个窝囊废手里,他连亲自将证据拿出来的勇气都没有,终日躲躲藏藏、鬼鬼祟祟。天下岂能交到这样一个无能的储君手里?!”
话到最后,声色俱厉。
苍璧惶恐不已,躬身应道:“阿郎,韩朝宗如此行事,不过因阿郎不在。是否尽快将这小子送去,指证东宫?”
“李亨并未派我烧毁证据,我去作证只能算栽赃,动不了他。”薛白道:“韦坚一案‘交构边镇大将’的大罪尚且未能废了他,这次更不行。唯有拿到李亨蓄养死士的证据,而我愿为右相当这个饵。”
话到这里,他已意识到自己说的多了、急了,李林甫是何等聪慧之人,岂需他这般解释?
果然,李林甫只以冷峻的眼神扫了他一眼,淡淡道:“少年郎心急,且待着,看看即便翻了案又能如何?”
~~
与李林甫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等消息并不舒服。
到了午间,相府有奴婢把酒菜送到偃月堂,并当着李林甫的面每道菜都小试了一口,他才放心享用。
薛白则站在那等着,看着窗外的景色,陷入了沉思。
待李林甫用过饭,在俏婢们的服侍下漱口、净手,当薛白不存在一般。
终于。
“阿郎,判了。”
“念。”
“柳勣、杜有邻等要犯,杖一百,家小流徙岭南,一应受柳勣行贿之官员,严惩不怠!”
“哈哈!翻了案还是死!翻案?”李林甫大笑,那双狠厉的眼神中似有了笑意,道:“莫说杖一百,杖三十便足以杖死他们。”
他又证明了一件事——他想要谁死,谁就得死,怎么挣扎都没用。
待到笑够了,他才问道:“你可知圣人为何如此?”
薛白方才一直在思考,开口便打算道一句“我愚钝,请右相赐教”,如此,李林甫便可装腔作势说上几句霸气之语。
但话到嘴边,他忽又想到,与其在李林甫面前藏拙,倒不如露拙。
“圣人也心知杜家是冤枉的。但圣人却要天下臣工看清楚,凡是想要投靠李亨以求飞黄腾达之人,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“竖子!”
“圣人要的太子是一個毫无助力的孤家寡人,等所有人都不敢亲近太子,太子也就没有了威胁。”
“够了!”李林甫拍案叱道:“妄自揣度圣意,你好大胆!”
薛白面无惧色,应道:“我若不大胆,如何敢助右相废太子?还有,右相已越来越难对付李亨了,因为李亨已经被右相羞辱了太多次,反而成了圣人眼里最软弱、最不具威胁的儿子!二月春风似剪刀,他的把柄都被右相剪了,他成了个毫无破绽的木头,最弱、也是最无懈可击,今日之后李亨的太子之位稳如泰山,皆拜右相所赐!”
“掌嘴!掌嘴!”
李林甫勃然大怒,倏地起身,指着薛白怒吼道。
一直以来,他自诩洞悉圣意,却唯独在这件事上太急了,此时才意识到薛白所言之理。
“右相千辛万苦,李亨却只要把支持他的人全部抛弃就能够得到圣人的满意。只有我的办法能拿到他的把柄……”
润奴一用力踹在薛白膝弯处。
薛白硬挨了,却不肯跪。
润奴大恼,脚下一勾,以胳膊卡住他的脖子,硬是将他摁倒在地。她力气极大,又有巧劲,翻身制住他,一手持匕挟他,一手抬起便要掌他嘴。
“右相!我正是在大缸中看明白了此间道理,翻案无用,李亨更是护不了任何人,故我欲投效右相,并不想在右相面前假装,愿助右相废了他!”
“那好。”
李林甫眼中精光闪烁,起身,踱步沉吟着,终于回过头道:“给你一个为老夫办事的机会,你来拿住李亨之罪证,真正能废了他的罪证。”
“好!”薛白道:“留下我,能成为梗在他喉咙里的刺,他早晚要拔刺。”
“你不错,明事理,率直坦荡,恩怨分明。”
润奴重重哼了一声,松开手,放薛白起身。
李林甫沉声道:“老夫于偃月堂中为国定计除奸,无往不利。今日定下除李亨之大计,你莫要辜负。”
薛白此时才知为何他让自己到偃月堂密谈,而不是屏退左右,竟只是为了讨个彩头。
“定不负右相重托!”
“你能体悟圣意,可是官宦子弟出身?”
“我于雪地昏死之后,前事一概忘了,此事千真万确。”
“也好,便当前事大梦一场,往后重新来过。”
“是。”薛白应了,却又拱手道:“我还有一事相请,恳请右相放过杜家。”
“莫得寸进尺。”
薛白道:“今李亨为自保而舍杜良娣。若杜家下场惨烈,世人只会认为是右相逼迫,衬得李亨可怜可叹。反之,若右相放过杜家,世人则只会道右相宽仁,李亨无情可笑。”
李林甫不悦道:“本相不需世人风评!”
“薛白与杜家皆不过蝼蚁而已,而蝼蚁有蝼蚁的用途!我听闻松赞干布向太宗皇帝求娶文成公主,太宗曾给他出过一个难题,要他将丝线穿过有九曲孔道的明珠,松赞干布百思不得其法,最后让蝼蚁系着丝线爬过九曲孔道,完成了穿线。”
薛白说着,再次郑重其事地行了个叉手礼,道:“薛白与杜家,愿为右相穿线。”
“还从未有人为本相办事是先提条件的。”李林甫字字森然,缓缓道:“你若想求死,本不该浪费本相时间。”
“我还是那六个字,恩必报、债必偿。”
“本相不是你能说服的。”
“却不知右相可有杜二娘消息?”
李林甫一听,脸色便沉下来。
他手底下有些人确实显得废物了。
“李亨好手段,看似无权无势,却事事瞒人耳目。”薛白道:“右相若能保了杜家,或可利用杜家找到杜二娘,从而找到其蓄养死士的证据。”
“你能做到?”
“五日之内,必给右相一个满意的结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