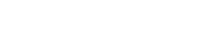太子别院。
李亨负手踱步,眼中忧虑重重,好不容易见张汀回来,连忙问道:“丈人可邀到薛白了?”
“没有。”张汀亦有些恼意,“我阿爷乃圣人表亲,薛白竟连他的面子也不给。”
“唉。”
“殿下何必如此紧张?卢杞被贬了正好,没人找出那些死士,眼下这一劫至少已过去了。”
“你懂什么?”李亨无意识地叱了一句,“引而未发,比当场揭穿还要可怕,两个死士在薛白手中,裴冕亦死于其手,愈晚事发,其祸愈烈。”
张汀瞥了一眼躬身在一旁的李静忠,悠悠道:“不如杀了他算了。”
“当初没杀成,眼下还如何杀,万一引得不可收拾。”李亨紧紧握拳,忍住了心中的怒意,方才道:“唯有不惜代价也要拉拢他。”
张汀不怎么喜欢李亨那许多儿女,问道:“为何圣人不肯让三娘下嫁薛白?也许是三娘没说她想嫁。”
“不,圣人是疑我,他就是认为我与义兄暗藏死士于长安,想再次打压我,自是不容我拉拢杨党。”李亨道:“要洗脱我与义兄的嫌疑,栽赃杂胡本是好办法,但杂胡圣眷太隆,只好退一步,以皇甫惟明结案,可此事又须有薛白相助,成了死结啊。”
这就是没有圣眷的结果。记住网址m.xiaoshuo.
杂胡、薛打牌、索斗鸡遇到更难的局面,或万事不做,或献宝,或认错,就能轻易过关,只有他这个太子不行,是真的一点圣眷都没有。
这边还在叹气,已有宫人匆匆赶来。
“圣人口谕,召太子兴庆宫觐见。”
李亨一听脸色就难看下来。
他太了解自己这个父皇了,想要见他,那就绝对不是好事。
果然。
到了兴庆宫,只见陪在李隆基身边的就没有一个忠正能臣,只有李林甫、安禄山。
“儿臣见……”
“免了吧。”李隆基已摆了摆手,淡淡道:“虚礼就不必行了。”
这些年,他只对李亨如此,认为这儿子嘴上的问安都是虚假的。
李亨只好起身,老实侍立在一旁。
只见今日勤政务本楼中难得没有歌舞,也许是杂胡述职时作些丑态,就能逗得这昏君开怀大笑吧。
此时若对比这一对父子,会发现他们从外表来看,仿佛年岁相差不大。
李隆基虽年老,看起来却精神奕奕,神采飞扬;李亨却比实际年纪看着衰老很多,透着一股垂垂老矣之气。
这个太子,长得就是一副很着急想要继位的样子。
只是看了儿子一眼,李隆基心情已略有不快,道:“继续谈,裴冕的案子说到哪了?”
“回圣人。”李林甫答道:“老臣已查清,此前之所以冤枉了薛白,确是因臣心中先作了推测,以此查证。”
“右相有何推测?”
“薛白曾献军器助王忠嗣……”
李亨当即打起精神准备应对,心道索斗鸡果然如此。
斗了这些年,彼此都是知根知底。
然而,索斗鸡这次竟是没有咄咄逼人,说到最后,反而道:“老臣仔细查访,却发现此案确与王忠嗣无关,他身在陇右,不可能使手下劲卒做到如此不留痕迹之地步。”
“右相以为是何人所为?”
“臣无能,未查到任何线索,请圣人责罚。”
李亨听着,忽感到一阵寒芒刺来,登时如坠冰窟,身子僵硬。
他发现自己准备好的说辞,一瞬间变得全无作用了。索斗鸡没指证他,圣人也未叱骂他,如何辩?
似乎只有片刻,又像是过了很久,李隆基爽朗而笑,叱骂道:“十郎这是有怨气啊,你女婿被朕杖责了,你就撂挑子,是吧?”
“臣绝无此心。”李林甫道:“元捴咎由自取,臣断无怨言。确是无能,未能查到线索。”
李亨先是听那“女婿”二字差点以为薛白已被索斗鸡先抢为女婿,其后回过神来,暗想索斗鸡何时真查过案,从来都是构陷而已。
李隆基眼见把索斗鸡吓得不敢行构陷之事,亦觉这次打压得有些过了,道:“放心大胆查!不论查到谁,朕绝不追究伱。”
“臣斗胆请圣人另选高明……”
~~
东市,澄心书铺。
姜澄脸上的笑意多了许多,手也不是笼在袖子里,而是捧着一迭纸。
“郎君请看,这是沤了十日之后造的竹纸,纸质比上次又有所提升,还有这张晒得更久些。”
“该还能有所进益。”薛白道。
即使已是十分不错的纸质,要得他一句夸赞却很难。
“若沤得久、晒得久有用,便往更久了试试。”
“郎君放心,那一池竹料还沤着呢。”
薛白道:“今日来还有一事问你,你可愿到将作监任职?”
姜澄吃惊,连忙表了忠心,道:“我是郎君的家仆,愿为郎君效劳。”
“你是杨家家奴,如今国舅拜相,正是要普及竹纸、大施拳脚,可在将作监为你谋个差事,只需说是否愿意。”
“郎君,可你这生意不赚钱了吗?”
“多少总归是有赚的,岂有志向重要?”
薛白见姜澄不因乍得前途而忘乎所以,心中有数。
等到他准备离开书铺,却见门外站着一个气质温润的年轻人,正是李泌。
两人对视一眼,颇有默契地笑了笑,薛白问道:“到书坊逛逛,还是去喝杯茶?”
李泌虽有心一观竹纸的工艺,今日来却有秘事要谈,不便在工匠身边走动,遂道:“我请薛郎品茶,如何?”
“却之不恭。”
说是品茶,两人一路出了春明门,到了长安东郊的一处农户家中坐下,却根本没有茶叶。
李泌也不在意,摸了几枚铜钱买了几个梨,就借着农户家中的陶釜煮梨水喝。
他不急着说话,从容不迫地做完了这些琐事,方才问道:“可是老凉、姜亥杀了裴冕?”
“嗯。”
李泌道:“皇甫惟明问罪时,我们保下这批老卒,原是作为证人,揭露王鉷盘剥军属一事,未曾想,致于如此地步。”
“先生认为当如何解决?”
“薛郎欲如何解决?”
薛白道:“我的想法,你肯定不认同。”
“废储必招致国本动荡。”
李泌没有任何焦虑之态,拿蒲扇轻扇着炉火,云淡风轻道:“殿下做错了许多事,好在时日还长,人力所不能解决的,岁月可以,你以为呢?”
薛白明白他的意思。
李隆基看起来寿命还长,很多事不必着急。李亨、李林甫的争斗其实是着相了,完全可以淡定一点。
说来,这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的盛世朝堂,若人人能如李泌这般平缓淡泊些,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
“看来,我比你更理解李亨的所做所为。”薛白道,“肉眼可见,他一定活不过圣人,若依着你这‘时日还长’的办法,岂能有翻身的一日?”
“此言,过于恶毒了。”
“好在只是言语上的恶毒?”
李泌挥动蒲扇,扫掉这些机锋,颇诚恳地说了些心里话,道:“我自视甚高,以辅国为平生志向。如今襄助殿下,非为让殿下重用我,凡事依我的办法而为,而是看如何作为对江山有益。薛郎以为,大唐换谁为储君能够更好?”
薛白道:“让你一步,我暂时不与你争这些。”
“多谢。”李泌道:“今日来,殿下希望我能劝你与东宫言归于好。”
“先生也想当媒婆,劝我娶和政县主。”
“上善若水,你既不愿,压迫你只会适得其反。”李泌道:“你曾献军器于陇右,想必不希望看到西北换将,局势动荡?”
“嗯。”
“那我来便是与你说,朝中这些争端真该缓一缓了。”说到这里,李泌指了指还在烧的陶釜,道:“水快干了,再烧,就要裂了。”
薛白问道:“我没有军情战报的来源,不知石堡城一战如何?”
“正缓缓图之。”
李泌熄了炉火,道:“王将军稳扎稳打,不忍士卒伤亡惨重,因此,虽有利器,攻城进展并不快,好在战果有。吐蕃为援石堡城,遣大军深入河陇屯区夺麦。陇右节度副使、都知关西兵马使、河源军使哥舒翰领兵应对,不久前,哥舒翰命王难得、杨景晖等人诱敌,设下埋伏,杀得五千吐蕃精锐骑兵匹马无回。此战,哥舒翰威震吐蕃,火速遣部将高秀岩、张守瑜返攻石堡城……”
当今大唐确实是名将如云。
薛白问道:“如此,还未攻下石堡城?”
“还在等消息传回。”李泌道:“当此时节,本不宜因朝中一些捕风捉影之事,而坏了边镇大事。”
薛白问道:“先生可有想过?如今朝中这些捕风捉影之事,正是为了等王忠嗣大胜归来,给他一个‘奖赏’。”
他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
但李泌又何尝没有这种忧虑?方才那番话里的意思,已透露出了一点关键信息。
陇右节度副使哥舒翰,已经能够接替王忠嗣的陇右节度使了。
“我想过与否不重要,眼下可否请薛郎莫要节外生枝。”李泌道,“将老凉、姜亥,以及裴冕留下之物安置妥当?”
“好。”
颇为干脆的一句回答,李泌稍微松了一口气,算是达成了今日的第一个共识。
李亨对此事很忧虑,但他这般简简单单就谈好了,他认为越简单的办法,错得越少。
有条不紊地把陶釜中的梨汤盛出来,分与薛白,李泌又问道:“听闻你前几日去了右相府,可是有喜讯了?若成亲,务必邀我。”
“没有,哥奴本打算炮制罪证构陷王忠嗣,我劝住了。”薛白饮了一口梨汤,比茶好喝,继续道:“这般说虽然像是在与你吹牛,但此事是真的。”
“答允了右相哪些条件?”
“简单,不与他争太多权,只争一点点。”
李泌笑问道:“裴冕案,右相打算如何交代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薛白脸皮厚,没显出半点不妥之色,“哥奴自有打算吧。”
李泌点了点头,道:“国舅拜相了也好,能多做实事,于社稷有利。”
薛白道:“我也是这般想的。”
这场谈话虽没有如李亨所愿完全拉拢薛白,但李泌至少说服了薛白让杨党不再对东宫过于逼迫,以免西北动荡。
李泌唯有一点想不通,觉得太过顺利了。
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为何。
~~
是日傍晚,李泌回到宅中,竟发现太子来访,不由十分讶异。
“殿下如何能来此处?”
李亨脸色很忧虑,开口满是苦涩之意,道:“因圣人命我查裴冕一案,特来向先生问计。”
他详细说了今日在兴庆宫的诸事。
李泌有一瞬间的失神,脑中迅速思考。
他以最快的速度,考虑过了牵扯此事的每一个人的立场。
杨党要的最简单,在朝堂上立足而已,因此薛白很快就答应了今日的请求,可见是愿意保王忠嗣;右相府则是出了一条毒计,想逼太子自罪、或罪于王忠嗣。
“殿下,圣人已经确定是殿下所为了。”李泌郑重道:“右相此举,几乎是挑明了说,人是东宫派人杀的,且圣人信了。”
“但不是。”李亨道:“那杀手不是我派的,是薛白……”
“回纥人是东宫臣属;老凉、姜亥亦出自东宫门下。殿下已无法向圣人自证,事到如今,心知肚明,只看殿下如何表态、圣人如何处置。”
“何意?”
“殿下要我直说?”
“你说。”
“好,圣人要的不是查案,而是一个理由,一个罢免王将军或处置殿下的理由。”
“哈?”李亨大笑,怒道:“我就知道,我说是胡儿杀的,他不信;索斗鸡说是薛白杀的,他还是不信。为什么?因为他心里早有答案,一说是我杀的,连证据都不要了,连脸都不要了!装都不装了!”
李泌默然。
事实很残酷,但确实如此。
臣子们各怀心思地炮制证据,到最后发现,天子就是不想听别的结果,等了一个多月,只等最后罪名落到东宫头上。
局面很糟糕,但李泌开口,却是道:“殿下,眼下并非最坏的情况。”
“先生有何高见?”李亨大喜。
“右相若对付王将军,则圣人必除王将军。但右相对付殿下,圣人却不会废了殿下……”
听到这里,李亨已经预感到他说的话自己不会爱听了。
果然。
“殿下只须与圣人坦诚即可破局。”
“坦诚?先生可想过我会如何?”
“泌愿以性命担保,必不至于废储。”
李亨僵住了。
他明白李泌的意思,他坦诚受罚,圣人的猜忌便可大幅减小,削弱东宫的手段则不至于太激烈。
打个比方,可能圣人原本要王忠嗣交出四镇兵权,如此一来说不定还能保留一个河东节度使之职以维持平稳。
代价是什么呢?
是将太子之罪公之于众,让一国诸君失去威严,甚至从此就被软禁。
李亨知道那昏君是如何想的,想活得长长久久,能活到儿子都死了,直接传位给皇孙更好。
只怕连李泌也是这般想的,所以才能说出“并非最坏的情况”这种话来,听得他心里发凉。
那是失望的感觉。
“先生……不能助我查出真相吗?”
“殿下分明看得清。”
李亨摇了摇头,转身便走。
他不可能去认这个罪,甚至那些人本就不是他杀的。但他也明白,指证任何人是凶手,圣人都不会相信。
好在,他也有办法破局。
~~
是夜,张汀忽听得呼喊,赶到院中一看,只见李亨竟是端起一盆井水浇在自己身上。
“殿下?!”
眼下已过了中秋,最是容易风寒入体之际。
李静忠亦是吓得不轻,匆忙去抢来一张小毯给李亨披上,哭道:“殿下为何如此?!殿下的身体可是国本啊!”
“人不救我……我自救。”李亨牙关打颤,抱着毯子,喃喃道:“我不会中他们的圈套,我不查不认……他们奈我何……我是储君,还能无故废了我不成?”
张汀当即明白过来,连忙吩咐道:“快,请御医,殿下病了!”
“是是,殿下病了……”
~~
十数日间,薛白似乎与朝中诸事无涉,却多了一个习惯。
他偶尔会去找李泌聊聊道法,实则是打听西北战报。
但李泌似乎也失去了消息来源,对攻石堡城的进展并不清楚,只是日渐忧虑。
一转眼就到了十月,西北终于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回长安,很快,满城皆知。
“高仙芝横穿险峻,奇袭小勃律国,一战灭国,俘虏小勃律王,及其王后,也就是吐蕃公主。拂菻、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!”
小勃律一介弹丸小国,倚仗着地域偏远,山川险峻,敢叛大唐而归吐蕃,隔断西域二十余国与大唐的联络。
遂有大唐将士千里奔袭,神兵天降,虽远必诛,大展国威。
可想而知,圣人是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。
在这个金秋,长安所有人谈论的都是西域这一战,评点着那一个个名将。
高仙芝相貌俊美,有勇有谋;李嗣业担任先锋,一柄陌刀所向无敌,浴血杀到小勃律王面前;封常清以布衣出身,运筹帷幄,调度有方;监军边令诚也是吃苦耐劳……
这等氛围中,薛白却知王忠嗣处境不好过。
此前未能攻下石堡城,若王忠嗣在此时节才攻下,难免要让人说是故意拖延,直到眼红高仙芝立功;若还不攻下,则显得太过无能。
没办法,谁让圣人最猜忌他,被攻讦而治罪是早晚的。
而东宫显然是打算不作为了。
薛白也只能尽力,看杨党到时能保到什么地步了。
就在长安这种气氛中,当他再一次找李泌要消息,李泌却给他看了一封抄录来的奏章。
“这是?”
“薛郎看吧。”李泌叹息,难得显出焦躁之感来。
薛白还是初次见他乱了道心。
纸上的字很漂亮,李泌书法放逸,有神仙风骨,但纸上抄录的内容却让人皱眉。
“文臣为将,怯当矢石,不若用寒畯胡人;胡人则勇决习战,寒族则孤立无党,陛下诚心恩洽其心,彼必能为朝廷尽死……”
薛白看得皱眉。
李泌起身踱了几步,到门边负手看着青天,喃喃道:“此为右相奏言,请圣人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。”
“尽用胡人?”
薛白良久无语。
都说李林甫能任相十余年,是大唐的能臣,能臣却能想出这种主意。
“边将尽用胡人,蠢得没边了。”
“问题是,圣人认为大善……”
今天写了万好几百字,求月票,求订阅~~
李亨负手踱步,眼中忧虑重重,好不容易见张汀回来,连忙问道:“丈人可邀到薛白了?”
“没有。”张汀亦有些恼意,“我阿爷乃圣人表亲,薛白竟连他的面子也不给。”
“唉。”
“殿下何必如此紧张?卢杞被贬了正好,没人找出那些死士,眼下这一劫至少已过去了。”
“你懂什么?”李亨无意识地叱了一句,“引而未发,比当场揭穿还要可怕,两个死士在薛白手中,裴冕亦死于其手,愈晚事发,其祸愈烈。”
张汀瞥了一眼躬身在一旁的李静忠,悠悠道:“不如杀了他算了。”
“当初没杀成,眼下还如何杀,万一引得不可收拾。”李亨紧紧握拳,忍住了心中的怒意,方才道:“唯有不惜代价也要拉拢他。”
张汀不怎么喜欢李亨那许多儿女,问道:“为何圣人不肯让三娘下嫁薛白?也许是三娘没说她想嫁。”
“不,圣人是疑我,他就是认为我与义兄暗藏死士于长安,想再次打压我,自是不容我拉拢杨党。”李亨道:“要洗脱我与义兄的嫌疑,栽赃杂胡本是好办法,但杂胡圣眷太隆,只好退一步,以皇甫惟明结案,可此事又须有薛白相助,成了死结啊。”
这就是没有圣眷的结果。记住网址m.xiaoshuo.
杂胡、薛打牌、索斗鸡遇到更难的局面,或万事不做,或献宝,或认错,就能轻易过关,只有他这个太子不行,是真的一点圣眷都没有。
这边还在叹气,已有宫人匆匆赶来。
“圣人口谕,召太子兴庆宫觐见。”
李亨一听脸色就难看下来。
他太了解自己这个父皇了,想要见他,那就绝对不是好事。
果然。
到了兴庆宫,只见陪在李隆基身边的就没有一个忠正能臣,只有李林甫、安禄山。
“儿臣见……”
“免了吧。”李隆基已摆了摆手,淡淡道:“虚礼就不必行了。”
这些年,他只对李亨如此,认为这儿子嘴上的问安都是虚假的。
李亨只好起身,老实侍立在一旁。
只见今日勤政务本楼中难得没有歌舞,也许是杂胡述职时作些丑态,就能逗得这昏君开怀大笑吧。
此时若对比这一对父子,会发现他们从外表来看,仿佛年岁相差不大。
李隆基虽年老,看起来却精神奕奕,神采飞扬;李亨却比实际年纪看着衰老很多,透着一股垂垂老矣之气。
这个太子,长得就是一副很着急想要继位的样子。
只是看了儿子一眼,李隆基心情已略有不快,道:“继续谈,裴冕的案子说到哪了?”
“回圣人。”李林甫答道:“老臣已查清,此前之所以冤枉了薛白,确是因臣心中先作了推测,以此查证。”
“右相有何推测?”
“薛白曾献军器助王忠嗣……”
李亨当即打起精神准备应对,心道索斗鸡果然如此。
斗了这些年,彼此都是知根知底。
然而,索斗鸡这次竟是没有咄咄逼人,说到最后,反而道:“老臣仔细查访,却发现此案确与王忠嗣无关,他身在陇右,不可能使手下劲卒做到如此不留痕迹之地步。”
“右相以为是何人所为?”
“臣无能,未查到任何线索,请圣人责罚。”
李亨听着,忽感到一阵寒芒刺来,登时如坠冰窟,身子僵硬。
他发现自己准备好的说辞,一瞬间变得全无作用了。索斗鸡没指证他,圣人也未叱骂他,如何辩?
似乎只有片刻,又像是过了很久,李隆基爽朗而笑,叱骂道:“十郎这是有怨气啊,你女婿被朕杖责了,你就撂挑子,是吧?”
“臣绝无此心。”李林甫道:“元捴咎由自取,臣断无怨言。确是无能,未能查到线索。”
李亨先是听那“女婿”二字差点以为薛白已被索斗鸡先抢为女婿,其后回过神来,暗想索斗鸡何时真查过案,从来都是构陷而已。
李隆基眼见把索斗鸡吓得不敢行构陷之事,亦觉这次打压得有些过了,道:“放心大胆查!不论查到谁,朕绝不追究伱。”
“臣斗胆请圣人另选高明……”
~~
东市,澄心书铺。
姜澄脸上的笑意多了许多,手也不是笼在袖子里,而是捧着一迭纸。
“郎君请看,这是沤了十日之后造的竹纸,纸质比上次又有所提升,还有这张晒得更久些。”
“该还能有所进益。”薛白道。
即使已是十分不错的纸质,要得他一句夸赞却很难。
“若沤得久、晒得久有用,便往更久了试试。”
“郎君放心,那一池竹料还沤着呢。”
薛白道:“今日来还有一事问你,你可愿到将作监任职?”
姜澄吃惊,连忙表了忠心,道:“我是郎君的家仆,愿为郎君效劳。”
“你是杨家家奴,如今国舅拜相,正是要普及竹纸、大施拳脚,可在将作监为你谋个差事,只需说是否愿意。”
“郎君,可你这生意不赚钱了吗?”
“多少总归是有赚的,岂有志向重要?”
薛白见姜澄不因乍得前途而忘乎所以,心中有数。
等到他准备离开书铺,却见门外站着一个气质温润的年轻人,正是李泌。
两人对视一眼,颇有默契地笑了笑,薛白问道:“到书坊逛逛,还是去喝杯茶?”
李泌虽有心一观竹纸的工艺,今日来却有秘事要谈,不便在工匠身边走动,遂道:“我请薛郎品茶,如何?”
“却之不恭。”
说是品茶,两人一路出了春明门,到了长安东郊的一处农户家中坐下,却根本没有茶叶。
李泌也不在意,摸了几枚铜钱买了几个梨,就借着农户家中的陶釜煮梨水喝。
他不急着说话,从容不迫地做完了这些琐事,方才问道:“可是老凉、姜亥杀了裴冕?”
“嗯。”
李泌道:“皇甫惟明问罪时,我们保下这批老卒,原是作为证人,揭露王鉷盘剥军属一事,未曾想,致于如此地步。”
“先生认为当如何解决?”
“薛郎欲如何解决?”
薛白道:“我的想法,你肯定不认同。”
“废储必招致国本动荡。”
李泌没有任何焦虑之态,拿蒲扇轻扇着炉火,云淡风轻道:“殿下做错了许多事,好在时日还长,人力所不能解决的,岁月可以,你以为呢?”
薛白明白他的意思。
李隆基看起来寿命还长,很多事不必着急。李亨、李林甫的争斗其实是着相了,完全可以淡定一点。
说来,这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的盛世朝堂,若人人能如李泌这般平缓淡泊些,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
“看来,我比你更理解李亨的所做所为。”薛白道,“肉眼可见,他一定活不过圣人,若依着你这‘时日还长’的办法,岂能有翻身的一日?”
“此言,过于恶毒了。”
“好在只是言语上的恶毒?”
李泌挥动蒲扇,扫掉这些机锋,颇诚恳地说了些心里话,道:“我自视甚高,以辅国为平生志向。如今襄助殿下,非为让殿下重用我,凡事依我的办法而为,而是看如何作为对江山有益。薛郎以为,大唐换谁为储君能够更好?”
薛白道:“让你一步,我暂时不与你争这些。”
“多谢。”李泌道:“今日来,殿下希望我能劝你与东宫言归于好。”
“先生也想当媒婆,劝我娶和政县主。”
“上善若水,你既不愿,压迫你只会适得其反。”李泌道:“你曾献军器于陇右,想必不希望看到西北换将,局势动荡?”
“嗯。”
“那我来便是与你说,朝中这些争端真该缓一缓了。”说到这里,李泌指了指还在烧的陶釜,道:“水快干了,再烧,就要裂了。”
薛白问道:“我没有军情战报的来源,不知石堡城一战如何?”
“正缓缓图之。”
李泌熄了炉火,道:“王将军稳扎稳打,不忍士卒伤亡惨重,因此,虽有利器,攻城进展并不快,好在战果有。吐蕃为援石堡城,遣大军深入河陇屯区夺麦。陇右节度副使、都知关西兵马使、河源军使哥舒翰领兵应对,不久前,哥舒翰命王难得、杨景晖等人诱敌,设下埋伏,杀得五千吐蕃精锐骑兵匹马无回。此战,哥舒翰威震吐蕃,火速遣部将高秀岩、张守瑜返攻石堡城……”
当今大唐确实是名将如云。
薛白问道:“如此,还未攻下石堡城?”
“还在等消息传回。”李泌道:“当此时节,本不宜因朝中一些捕风捉影之事,而坏了边镇大事。”
薛白问道:“先生可有想过?如今朝中这些捕风捉影之事,正是为了等王忠嗣大胜归来,给他一个‘奖赏’。”
他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
但李泌又何尝没有这种忧虑?方才那番话里的意思,已透露出了一点关键信息。
陇右节度副使哥舒翰,已经能够接替王忠嗣的陇右节度使了。
“我想过与否不重要,眼下可否请薛郎莫要节外生枝。”李泌道,“将老凉、姜亥,以及裴冕留下之物安置妥当?”
“好。”
颇为干脆的一句回答,李泌稍微松了一口气,算是达成了今日的第一个共识。
李亨对此事很忧虑,但他这般简简单单就谈好了,他认为越简单的办法,错得越少。
有条不紊地把陶釜中的梨汤盛出来,分与薛白,李泌又问道:“听闻你前几日去了右相府,可是有喜讯了?若成亲,务必邀我。”
“没有,哥奴本打算炮制罪证构陷王忠嗣,我劝住了。”薛白饮了一口梨汤,比茶好喝,继续道:“这般说虽然像是在与你吹牛,但此事是真的。”
“答允了右相哪些条件?”
“简单,不与他争太多权,只争一点点。”
李泌笑问道:“裴冕案,右相打算如何交代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薛白脸皮厚,没显出半点不妥之色,“哥奴自有打算吧。”
李泌点了点头,道:“国舅拜相了也好,能多做实事,于社稷有利。”
薛白道:“我也是这般想的。”
这场谈话虽没有如李亨所愿完全拉拢薛白,但李泌至少说服了薛白让杨党不再对东宫过于逼迫,以免西北动荡。
李泌唯有一点想不通,觉得太过顺利了。
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为何。
~~
是日傍晚,李泌回到宅中,竟发现太子来访,不由十分讶异。
“殿下如何能来此处?”
李亨脸色很忧虑,开口满是苦涩之意,道:“因圣人命我查裴冕一案,特来向先生问计。”
他详细说了今日在兴庆宫的诸事。
李泌有一瞬间的失神,脑中迅速思考。
他以最快的速度,考虑过了牵扯此事的每一个人的立场。
杨党要的最简单,在朝堂上立足而已,因此薛白很快就答应了今日的请求,可见是愿意保王忠嗣;右相府则是出了一条毒计,想逼太子自罪、或罪于王忠嗣。
“殿下,圣人已经确定是殿下所为了。”李泌郑重道:“右相此举,几乎是挑明了说,人是东宫派人杀的,且圣人信了。”
“但不是。”李亨道:“那杀手不是我派的,是薛白……”
“回纥人是东宫臣属;老凉、姜亥亦出自东宫门下。殿下已无法向圣人自证,事到如今,心知肚明,只看殿下如何表态、圣人如何处置。”
“何意?”
“殿下要我直说?”
“你说。”
“好,圣人要的不是查案,而是一个理由,一个罢免王将军或处置殿下的理由。”
“哈?”李亨大笑,怒道:“我就知道,我说是胡儿杀的,他不信;索斗鸡说是薛白杀的,他还是不信。为什么?因为他心里早有答案,一说是我杀的,连证据都不要了,连脸都不要了!装都不装了!”
李泌默然。
事实很残酷,但确实如此。
臣子们各怀心思地炮制证据,到最后发现,天子就是不想听别的结果,等了一个多月,只等最后罪名落到东宫头上。
局面很糟糕,但李泌开口,却是道:“殿下,眼下并非最坏的情况。”
“先生有何高见?”李亨大喜。
“右相若对付王将军,则圣人必除王将军。但右相对付殿下,圣人却不会废了殿下……”
听到这里,李亨已经预感到他说的话自己不会爱听了。
果然。
“殿下只须与圣人坦诚即可破局。”
“坦诚?先生可想过我会如何?”
“泌愿以性命担保,必不至于废储。”
李亨僵住了。
他明白李泌的意思,他坦诚受罚,圣人的猜忌便可大幅减小,削弱东宫的手段则不至于太激烈。
打个比方,可能圣人原本要王忠嗣交出四镇兵权,如此一来说不定还能保留一个河东节度使之职以维持平稳。
代价是什么呢?
是将太子之罪公之于众,让一国诸君失去威严,甚至从此就被软禁。
李亨知道那昏君是如何想的,想活得长长久久,能活到儿子都死了,直接传位给皇孙更好。
只怕连李泌也是这般想的,所以才能说出“并非最坏的情况”这种话来,听得他心里发凉。
那是失望的感觉。
“先生……不能助我查出真相吗?”
“殿下分明看得清。”
李亨摇了摇头,转身便走。
他不可能去认这个罪,甚至那些人本就不是他杀的。但他也明白,指证任何人是凶手,圣人都不会相信。
好在,他也有办法破局。
~~
是夜,张汀忽听得呼喊,赶到院中一看,只见李亨竟是端起一盆井水浇在自己身上。
“殿下?!”
眼下已过了中秋,最是容易风寒入体之际。
李静忠亦是吓得不轻,匆忙去抢来一张小毯给李亨披上,哭道:“殿下为何如此?!殿下的身体可是国本啊!”
“人不救我……我自救。”李亨牙关打颤,抱着毯子,喃喃道:“我不会中他们的圈套,我不查不认……他们奈我何……我是储君,还能无故废了我不成?”
张汀当即明白过来,连忙吩咐道:“快,请御医,殿下病了!”
“是是,殿下病了……”
~~
十数日间,薛白似乎与朝中诸事无涉,却多了一个习惯。
他偶尔会去找李泌聊聊道法,实则是打听西北战报。
但李泌似乎也失去了消息来源,对攻石堡城的进展并不清楚,只是日渐忧虑。
一转眼就到了十月,西北终于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回长安,很快,满城皆知。
“高仙芝横穿险峻,奇袭小勃律国,一战灭国,俘虏小勃律王,及其王后,也就是吐蕃公主。拂菻、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!”
小勃律一介弹丸小国,倚仗着地域偏远,山川险峻,敢叛大唐而归吐蕃,隔断西域二十余国与大唐的联络。
遂有大唐将士千里奔袭,神兵天降,虽远必诛,大展国威。
可想而知,圣人是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。
在这个金秋,长安所有人谈论的都是西域这一战,评点着那一个个名将。
高仙芝相貌俊美,有勇有谋;李嗣业担任先锋,一柄陌刀所向无敌,浴血杀到小勃律王面前;封常清以布衣出身,运筹帷幄,调度有方;监军边令诚也是吃苦耐劳……
这等氛围中,薛白却知王忠嗣处境不好过。
此前未能攻下石堡城,若王忠嗣在此时节才攻下,难免要让人说是故意拖延,直到眼红高仙芝立功;若还不攻下,则显得太过无能。
没办法,谁让圣人最猜忌他,被攻讦而治罪是早晚的。
而东宫显然是打算不作为了。
薛白也只能尽力,看杨党到时能保到什么地步了。
就在长安这种气氛中,当他再一次找李泌要消息,李泌却给他看了一封抄录来的奏章。
“这是?”
“薛郎看吧。”李泌叹息,难得显出焦躁之感来。
薛白还是初次见他乱了道心。
纸上的字很漂亮,李泌书法放逸,有神仙风骨,但纸上抄录的内容却让人皱眉。
“文臣为将,怯当矢石,不若用寒畯胡人;胡人则勇决习战,寒族则孤立无党,陛下诚心恩洽其心,彼必能为朝廷尽死……”
薛白看得皱眉。
李泌起身踱了几步,到门边负手看着青天,喃喃道:“此为右相奏言,请圣人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。”
“尽用胡人?”
薛白良久无语。
都说李林甫能任相十余年,是大唐的能臣,能臣却能想出这种主意。
“边将尽用胡人,蠢得没边了。”
“问题是,圣人认为大善……”
今天写了万好几百字,求月票,求订阅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