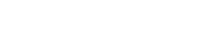满唐华彩正文卷第章担责上元夜御宴,玉真公主也在场。
她不愿引人注目,坐在侧殿稍远的位置打算观赏歌舞,倒没想到,这夜最热闹的不是歌舞,而是有人在殿上直言劝谏圣人。
自从那几个执拗的专权宰相致仕后,她已十余年未见到如此情形了。
当薛白被押出大殿,她转头往身后看了一眼,只见两个弟子皆愣愣看着殿门方向,仿佛魂都被带走了。
之后,安禄山又开始跳胡旋舞。
玉真公主素来讨厌这种丑态,以袖掩目,向两个弟子道:“既然待不住了,一会歇宴时你们便先告退吧。”
“真的吗?”
李季兰是初次来上元宴,并不觉得有意思,至少目前为止还未听到好的诗词歌赋,遂道:“弟子……”
“弟子是有些乏了。”李腾空担心她说出甚不像样的话来,淡淡应了一句。
“是的。”李季兰拿手捂在嘴上,假装打了个哈欠,“有些乏了。”
待鼓声停歇,圣人打完鼓要去更衣,御宴暂歇,众人交头接耳地小声嘀咕,说的都还是方才薛白、李泌直谏之事。
根本没人在意安禄山足足转了五十圈。
李季兰退出大殿,望向灯火通明的长安城,不由被眼前的情景震撼,道:
“腾空子,我们去何处找薛郎?”
“谁说要找他了。”李腾空答着,抬眼看长安,眸中却带着深深的担心。
她转身环顾,见一群官员拥着李林甫往庑房去歇息,遂道:“你去皎奴那等我。”
“欸,你去哪?”
李腾空已快步向她阿爷那边跑去,在门口被拦了一下,表明了身份才得以入内。
庑房中,李林甫正在对许多官员吩咐着。
“北衙、南衙已派人去找李延业、凤迦异,伱等务必先查清此事。”
“依下官看,薛白必与此事脱不了干系。”
“十郎,你带人去找到薛白……”
李林甫说着,忽停下话头,看着李腾空进来,淡淡道:“你如何来了?”
在一众官员面前,李腾空很给他面子,只问了一句。
“阿爷,可否让女儿帮阿兄找人?”
父女二人都明白对方的心思,李林甫想了一会儿,叹道:“去吧,让他好自为之。”
“喏。”
李岫行了礼,带着妹妹退出了庑房,拿令牌办好了离开兴庆宫的事宜。
出了通阳门,只见薛徽正在分派人手搜城。
“不得安生啊。”李岫感慨道,“你说,他为何就不能消停些?”
“父兄与他皆是朝廷命官。”李腾空语气略带悲悯,道:“官若消停了,也许生黎庶民便不得消停?”
“女大不中留啊,胳膊肘总往外拐。”
“阿兄,我亲眼见了殿上所发生的一切,由感而发。然,凡所言不合你意,则是我无主见,凡事向着薛白。阿兄、阿爷,甚至圣人,已是任何一句忤逆之言都听不得了?”
李岫没有马上回答,好一会才苦笑道:“这不是已经开始忤逆了吗?”
他一向顺服于李林甫,因此最能敏锐地感受到天宝九载这个上元夜有一个重要的改变——朝中有些人,已开始不再奉迎圣人了。
“薛打牌”“薛唱歌”忽然摇身一变,成了“薛直谏”“薛敢言”了,而且竟还有人敢与之合作。
朝堂就像狼群,一察觉到圣人、宰相愈发老了,小狼崽子们已蠢蠢欲动。
王焊登高一呼的那声“萎厥”余音还未消散。
“十郎,找到了。”
“在哪?”
“他往东市去了。”
“走。”
长安城灯火通明,恍如白昼,走在路上连灯笼都不必提。一行人向西南方向走去,进了东市,前方愈来愈热闹。
“他在哪?”李岫不得不提高音量,凑在属下人的耳边问道。
“十字街口。”
远处正有人在舞火鸟,赢得一阵吆喝。
李腾空忽感觉到了什么,抬起头看去,只见有一人正踩着高跷,走在人群头上。
这场景似曾相识,天宝六载的上元节她与薛白也是到东市来,想寻一个药铺。
“就在前面了,他该是要去丰汇行,虢国夫人的产业。”
“带路。”
李岫抬眼看去,只见一家商铺前挂着金币形状的花灯,正要过去,却听得禀报说薛白往前走了。
好不容易拨开人群,出了东市,他正要让手下加快脚程。
“十郎,人被薛徽请走了。”
“该死。”李岫吩咐道,“盯紧薛徽的人,看他们查到什么。”
~~
夜愈深,长安愈亮。
两名女冠领着随从在东市附近走走逛逛,时而抬头看看不远处的望火楼,时而买些布匹、首饰。
末了,她们在小摊边买了两盏花灯,各自要了一支笔,在灯纸上写写画画。
李季兰擅写诗,今年却懒得去雕琢字句,而是执笔轻描,勾勒出了一个少年郎的形象。
李腾空则是陪她打发时间,默写着《道德经》。
“道可道,非常道?”李季兰转头看了一眼,大摇其头,嘟囔道:“上元节,你提着这样一盏花灯?”
“画花灯亦是修行。”
“是我太傻了,使你总拿这种假话敷衍我。”
李腾空心无杂念,只顾写经文,在这灯火阑珊的夜色中显得素雅而独特。
忽然,不远处有歌声传来。
“是薛郎的词。”李季兰站起身来,仔细倾听,之后抬头看向望火楼,呢喃自语道:“他三年前许下志向,要仗义执言、奋不顾身,站在那灯火阑珊处。”
李腾空愣了愣。
耳畔,那歌声已唱到了第二遍,“蛾儿雪柳黄金缕,笑语盈盈暗香去。”
世人都在为之沉醉,却唯她知道,那是他写给她的。
李腾空低下头,接着她抄写的《道德经》,在后面写了一首小诗。
“我有方寸心,无人堪共说。”
“遣风吹却云,言向天边月。”
抬头看去,柳树梢头,一轮明月正圆,清辉遍地。
忽然,
“薛白下来了。”
“有金吾卫跟着,不好拿下。”
“别让薛徽的人看到我们。”
李岫既知薛徽的心意,今夜唯有暂且作罢。
“早晚有护不住他的时候,走吧。”
李腾空回过头看去,只见薛白走到方才那个小摊边,买了一盏花灯,执笔写了一会儿,提着花灯自远走。
~~
清晨,宣阳坊,薛宅。
青岚才安顿了薛白睡下,却听婢子通禀门外有两位女冠求见。
“她们是郎君的好友,也就是郎君外放了一年,你们才不认得她们。”
青岚颇为高兴,亲自到内堂去迎。
“腾空子,季兰子,你们怎来了?”
“我们有桩事想要提醒薛郎。”李腾空道。
她知道薛白昨夜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上,因此,她才会去见李林甫、才会与李岫一起跟着薛白,为的是保护他。
右相府对他的态度还不确定,可能会容忍,可能会除掉,她需要提醒他几句。
青岚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,连忙道:“那我去唤郎君出来。”
“好。”
李季兰见青岚跑开,问道:“腾空子,有镜子吗?我可是熬了一夜。”
“你很美。”
“真的?”
李季兰已发现了内堂上摆着一枚扬州水心镜,于是走了过去。
李腾空一转眼,目光却落在了地上那盏熄灭的花灯上,见上面题着的是一首诗。
那是薛白方才在东市买灯时随手写上去的,当时隔得虽远,她却能感受到他写诗时有些惆怅。
因为丢了官,很不开心吧?
她没忍住,走上前,提起那盏花灯看了一眼。
那是首五言律诗,他的一手颜楷像他的人一样俊逸隽永。
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”
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
“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”
“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。”
~~
一滴泪水划过细腻的脸颊,落在袖子上。
李腾空努力噙住泪,一回头,竟见薛白不知何时已站在她身后了。
她吓了一跳,连忙放下花灯,不知所措。
方才想着心事,不知时间过了多久,薛白似乎已经在那里喊了她很久。但她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失态,干脆快步出了内堂,走进庭院中的小径,吸着鼻子。
“腾空子?”
“那个……季兰子有话与你说。”
李腾空找了个借口,等了一会,李季兰也不懂得来解围,身后没了声响。
她回头瞥了一眼,见到薛白就守在不远处,她又迅速背过身去。
“腾空子。”
“我看到那诗……”
“嗯。”
“我就不该看。”李腾空抹了抹泪,显得有些倔强,“我修我的道,本是自在……偏看到你的心意,反而容易觉得遗憾、委屈……”
“是我不该写那首诗。”
“你乱了我心境。”李腾空没忍住,用哭腔抱怨了薛白一句。
这种蛮不讲理的抱怨,是小女子对最亲密之人才会用的。
她说完才意识到,愈发慌张,强自镇定,道:“我要好好修道,你也要成亲了,不可再写这种诗句。”
“好,昨夜,我……确是想到你。”
“不许。”
“好。”薛白感受她的情绪,缓缓道:“你放心,我只是有感而发,是待好友的态度。”
“嗯,我也只是视你为好友。”
“我这人,最在乎的是自己,始终专注于自己。”薛白说着,逐渐坦诚,“故而我虽心中有你,却不会为你而改变立场、投靠右相府。我首先是我,才会偶尔……有些想念,偶尔。”
“嗯。”李腾空也镇定下来,道:“我也是,首先我是我。我生于相府,修道积德、赎我之罪孽,为我平生所求,我也不会为你改变。”
“好。”
一番话之后,两人反而像更疏远了些。
李腾空听到了身后有脚步声响起,似乎是薛白觉得她足够坚强,于是要离开了。
她不由回过身,问道:“你偶尔……也……也会想念我吗?”
~~
“腾空子?”
李季兰等了一会儿,出了内堂,往庭院里的小径走去,路上很小声地唤了一句。
她其实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知方才李腾空发着呆,被薛白唤了好几声之后跑掉了。也许是太困站在那睡着,被梦魇惊到了?
转过小径,眼前两道人影映入眼帘,李季兰眼眸一瞪,大吃一惊。
“呀。”
“季兰子。”
“你们……我……”李季兰拿手捂在嘴上,假装打了个哈欠,道:“我好困。”
“是啊。”
三人遂往内堂走去。
薛白道:“对了,你们过来找我,有话要说?”
“是,你得罪了我阿爷,又触怒了圣人,明枪易躲,暗箭难防。是否先避一避?”
“避往何处?”
“我们想了一个去处。”李季兰看向李腾空想作眼神交流,李腾空却低着头,她只好道:“王屋山如何?”
“王屋山?”
“灵都观是师父的观邸,谁都不能在其中害你。”
薛白笑着摇摇手,道:“不敢劳玉真公主,我如今无官无职,与人无碍,当不至于有性命之忧。”
“薛郎真罢官了吗?那接下来做什么?”李季兰问道:“写戏文吗?”
“倒是有些想法,该是……炼丹。”
“嗯?”李腾空问道:“你也修道?”
“应该是只炼丹,不修道。”
李腾空修道、习医,对炼丹术也有所了解,并不喜欢那些药材以外的丹药,此时便颇为不解薛白为何会对炼丹感兴趣。
李季兰却很高兴,连忙道:“那我们也帮忙吧?腾空子可有丹炉圣手之称。”
“我哪有。”
“好。”薛白其实已经捉了一个这方面很厉害的道士,却也没推拒她们的好意,“近来得空,还得多多向两位道长请教。”
雪后天晴,才哭过的李腾空心情蓦然好起来。
~~
“阿爷,还有一件事……十七娘去了薛白宅。”
从花萼楼回到右相府,李林甫显得很疲倦,他却还得听李岫禀报上元夜之后发生的诸多事务。
“随他们去吧,你莫管十七娘,两情相悦,你拦得住吗?”
“是。”李岫正要退下,才想起南诏质子之事还没得到明确回答,遂停下脚步问道:“凤迦异之死?”
“元月,有几份奏章。”李林甫道:“群臣请封西岳,圣人已批允了。”
李岫一愣。
“华岳祠已建好,华山道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凿。封禅就在十月,你说南诏叛了?”
“那……”
“叛了也给圣人摁下去。”
“喏!”
李岫终于得了明确的回复,连忙退了出去,赶往议事堂,把李林甫的意思对诸官员吩咐下去。
分为两个方面,一方面传中书政令至西南,着鲜于仲通、张虔陀等官员,务必盯紧阁罗凤,绝不允许南诏出现叛乱;另一方面,严令南衙、京兆府等京城官员,封锁消息,不能让凤迦异叛逃之事闹大……
~~
李林甫难得睡得很沉,但其实到中午也就醒来了。
醒来时,他想到薛白已经丢了官,陈希烈、杨国忠皆已顺服,王鉷之死造成的相位动摇终于过去,让人轻松不少。
至于南诏叛或不叛,这并不重要,因为朝廷早就有所提防,阁罗凤一旦有异心,朝廷在西南的布置足以轻易拿下他。
就在天宝八载,他还命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率军入南诏,取安宁城以及盐井,控制南诏的盐也就控制了其命脉。
换言之,西南不可能有大动荡,没必要对阁罗凤是否有叛心之事小题大作,以免影响到封禅西岳的大事。
这才是他必胜的原因,可惜,薛白等人不懂这些内情。
眼下的问题只在于该牵连到谁为止……张垍?李亨?
李延业之死显然有蹊跷,可以顺着往下查,再掀一场对付东宫的大案。
另外,李林甫也在考虑永王是否适合为储位一事。
“阿爷醒了吗?”院外传来了李岫的声音。
“何事?”
李林甫敏锐地预感到又出事了。
果然,当李岫匆匆进来,手里便拿了一张邸报。
~~
傍晚,薛白醒来,只见有人正坐在榻边的凳子上看着他,是明珠。
“为何这样?怪吓人的。”
“瑶娘担心你的安危,派人来保护你。”
“那也不必如此。”
“我与皇甫小娘子说是来看着你的,她便搬了凳子让我坐。”
青岚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,窘迫道:“我以为看着就是坐在这看着嘛……”
薛白道:“玉瑶是看到邸报了?”
“是,瑶娘说郎君有些过了。”
“给我看看。”
明珠遂从怀中拿出一张邸报递了过来。
薛白其实早就知道内容,但还是再看了一遍。最重要的消息有两则,一说南诏质子凤迦异叛逃,南诏与吐蕃勾结,背叛大唐,已是不争之事实;二说李林甫蒙蔽圣听,粉饰太平,翰林李泌、御史薛白等直臣上元夜进谏,被罢官。
俱为事实。
如薛白与杜妗所言,此事一旦召告天下,哪怕做得再隐秘,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他做的。
这也是杨玉瑶派人来保护薛白的原因。
“郎君近来还是先到虢国夫人府去住一段时日。”明珠劝道。
青岚道:“我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。”
“这次,玉瑶也保不了我,但放心吧,我大抵不会有事。”
薛白这边从容镇定地说完,那边却已有吏员带来了吏部的文书。
“天宝九载制,授薛白海阳县令告身!”
明珠跟在薛白身后出来,听得这一声吆喝,吃了一惊,低下头自思量着也不知瑶娘该有多生气。
“监察御史薛白,司计臣俊言,有应辨才,实堪励俗,故从优秩,今授铜印,俾宰海阳。”
薛白似乎不敢去接告身,推辞道:“可我已经辞官了。”
“并未听闻过薛郎辞官一事,反而恭喜薛县令升官了,海阳县乃潮阳郡之治所,县令可是七品官。”
~~
入夜。
上元节长安城有三个夜晚不会宵禁,这是第二个夜晚。
灯市依旧繁华,没有因为朝堂上的纷争而受影响,市井间反而多了谈资。
这样的夜晚,就连十王宅里的诸王也能够出来逛逛……天宝五载的大案也就是因此而起的。
庆王李琮已经换了衣服,准备带着儿孙们去看看灯市。
但他还在等一个消息。
“大郎。”
“如何?”
“出事了,他被贬往潮阳,傍晚时得的告身,之后便称得了风寒,装病不起。”
李琮问道:“贬往潮阳?他还躲得了吗?”
“不知,大郎是否不去见他为宜,眼下这局面……”
眼下这局面怎么看都是李林甫已经赢了,直谏的几个官员贬的贬、投的投。
但李琮不由总是想起李亨先于自己走到殿中据理力争的场景,那一瞬间,让他觉得自己不如李亨。
“不,我若不去出面,他投靠李林甫就能免于被贬,走吧。”
他知道薛白还有别的选择,皇子很多,且东宫、右相府都在拉拢薛白。从御宴上薛白的态度就能看出来,对他虽有失望,却很平静。
若不去,损失的是他。
李琮遂出了门,去东市看花灯。
他一身普通襕袍打扮,走在人群中远看并不显眼,但近看脸上的疤痕却颇让人触目惊心。
于是,路过一个卖面具的小摊时,他便买了个面具,选了一只猴,虽然他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猴……他的脸就是被猴类抓伤的。
前方有人在舞灯,李琮带着家人避入了一间酒楼,要了个雅间。
而在他身后,有人正不远不近地跟着,寻找着掀起一桩大案的证据。
~~
仅一柱香之后,李琮已是一身小厮打扮,从酒楼后院穿过秘道,走进了一座闹中取静的院落。
他看着十分镇静,心底却隐有些不安。
前方,一道门被推开,李琮整理了衣衫,以及脸上的面具,长吐一口气,迈步走了进去。
薛白竟就在屋内,他本该在家中装病,且被无数人盯着,出来会面是极危险的一件事,而他身边还站着一个气质冷艳的女子。
李琮第一眼没认出这女子是谁,再一看,心中不由讶然,认出她是原来的太子良娣杜妗。
薛白见有人来,竟是伸手在杜妗腰上拍了拍,有个安抚的动作。
“庆王。”
回答薛白的是一张毫无表情的猴面具。
李琮没有说话,在面具的掩盖下,显得很有威严。
但他的背脊已经发凉了。
屋内还有很多个彪悍的大汉,全部站在那,看着薛白与杜良娣卿卿我我,听着他喊“庆王”,让他感到十分危险。
“你们想知道卖命做事能换来什么,今夜我便告诉你们,是从龙之功!这位便是当今圣人之长子,庆王殿下。”
薛白说着,走到李琮面前执礼,道:“还不对庆王见礼?”
“见过庆王!”
李琮想让众人小声些,但这一刻,天潢贵胄的血液在他身体里流淌起来。
他竟是以浑厚而温和的声音道:“诸位壮士既愿与本王生死与共,何必多礼。”
“圣人老了,受奸臣蒙蔽,任用贪官横征暴敛,又听信谗言,一日杀三子。是庆王,收养太子之遗孤,苦心孤诣,欲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之将倾,保大唐盛世之基业。而社稷正统只在庆王一系,何人敢有异言?!”
薛白一番话,屋中众人俱是精神一振,因知自己辅佐的才是大唐正统。
连李琮也振奋起来,感受到自己离储位更近了一步。
他看着薛白那双灼灼的目光,点了点头,缓缓把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。
不需要更多的证明,他这张满是伤疤的脸,就是他身份的最好明证。
“本王问你们,是想要一个面容皎好但昏庸懦弱的储君,还是一个容貌虽有伤却心系黎庶的储君?”
“我等誓为庆王效死!”
听得这样一句并不算整齐的喊话,李琮竟有些感动,郑重道:“本王绝不负诸位壮士!”
“我为庆王引见。”薛白先指了一个面带风霜的汉子,道:“樊牢,曾经在怀州当过捉不良帅。这次便是他查到凤迦异叛逃之事,让我们能提前掌握消息……”
人群中,任木兰不由笑了一下。
她知道,樊牢才不是查到了凤迦异叛逃,事实上就是樊牢带着凤迦异叛逃。
之所以知道,因为就是她扮成奴婢混入李延业府上,偷偷摸进李延业屋中一刀将其结果了,偷出了令牌以及重要证据。
这次到长安,她发现,长安虽好,但长安人不像她能玩命。
至于眼前这个庆王,显然没把她这个小丫头当一回事,看都不看她一眼,只顾着用目光勉励那些壮汉们。
……
见过了这些死士,李琮则与薛白、杜妗单独谈。
“听说哥奴将你贬到潮阳郡了,你可有应对?”
“不是我需要应对。”薛白道,“而是等到哥奴把控不了局面的时候,我们该如何接手国事。眼下不过是破晓前的黑暗罢了。”
“真的?”
李琮一挑眉,惊讶于结果竟比他预想中好得多。
“薛郎能确定?”
“我拿到张虔陀的失踪的奏章了,阿伯可要看看?”
“好。”
李琮很欣慰,薛白终于又与他重新亲近起来。
之后,几封抄录文书便递到了他的面前。
“西南形势,只怕比满朝重臣预想中都糟得多。当此时节,唯阿伯可力挽狂澜、担负起皇长子之重责了……”
她不愿引人注目,坐在侧殿稍远的位置打算观赏歌舞,倒没想到,这夜最热闹的不是歌舞,而是有人在殿上直言劝谏圣人。
自从那几个执拗的专权宰相致仕后,她已十余年未见到如此情形了。
当薛白被押出大殿,她转头往身后看了一眼,只见两个弟子皆愣愣看着殿门方向,仿佛魂都被带走了。
之后,安禄山又开始跳胡旋舞。
玉真公主素来讨厌这种丑态,以袖掩目,向两个弟子道:“既然待不住了,一会歇宴时你们便先告退吧。”
“真的吗?”
李季兰是初次来上元宴,并不觉得有意思,至少目前为止还未听到好的诗词歌赋,遂道:“弟子……”
“弟子是有些乏了。”李腾空担心她说出甚不像样的话来,淡淡应了一句。
“是的。”李季兰拿手捂在嘴上,假装打了个哈欠,“有些乏了。”
待鼓声停歇,圣人打完鼓要去更衣,御宴暂歇,众人交头接耳地小声嘀咕,说的都还是方才薛白、李泌直谏之事。
根本没人在意安禄山足足转了五十圈。
李季兰退出大殿,望向灯火通明的长安城,不由被眼前的情景震撼,道:
“腾空子,我们去何处找薛郎?”
“谁说要找他了。”李腾空答着,抬眼看长安,眸中却带着深深的担心。
她转身环顾,见一群官员拥着李林甫往庑房去歇息,遂道:“你去皎奴那等我。”
“欸,你去哪?”
李腾空已快步向她阿爷那边跑去,在门口被拦了一下,表明了身份才得以入内。
庑房中,李林甫正在对许多官员吩咐着。
“北衙、南衙已派人去找李延业、凤迦异,伱等务必先查清此事。”
“依下官看,薛白必与此事脱不了干系。”
“十郎,你带人去找到薛白……”
李林甫说着,忽停下话头,看着李腾空进来,淡淡道:“你如何来了?”
在一众官员面前,李腾空很给他面子,只问了一句。
“阿爷,可否让女儿帮阿兄找人?”
父女二人都明白对方的心思,李林甫想了一会儿,叹道:“去吧,让他好自为之。”
“喏。”
李岫行了礼,带着妹妹退出了庑房,拿令牌办好了离开兴庆宫的事宜。
出了通阳门,只见薛徽正在分派人手搜城。
“不得安生啊。”李岫感慨道,“你说,他为何就不能消停些?”
“父兄与他皆是朝廷命官。”李腾空语气略带悲悯,道:“官若消停了,也许生黎庶民便不得消停?”
“女大不中留啊,胳膊肘总往外拐。”
“阿兄,我亲眼见了殿上所发生的一切,由感而发。然,凡所言不合你意,则是我无主见,凡事向着薛白。阿兄、阿爷,甚至圣人,已是任何一句忤逆之言都听不得了?”
李岫没有马上回答,好一会才苦笑道:“这不是已经开始忤逆了吗?”
他一向顺服于李林甫,因此最能敏锐地感受到天宝九载这个上元夜有一个重要的改变——朝中有些人,已开始不再奉迎圣人了。
“薛打牌”“薛唱歌”忽然摇身一变,成了“薛直谏”“薛敢言”了,而且竟还有人敢与之合作。
朝堂就像狼群,一察觉到圣人、宰相愈发老了,小狼崽子们已蠢蠢欲动。
王焊登高一呼的那声“萎厥”余音还未消散。
“十郎,找到了。”
“在哪?”
“他往东市去了。”
“走。”
长安城灯火通明,恍如白昼,走在路上连灯笼都不必提。一行人向西南方向走去,进了东市,前方愈来愈热闹。
“他在哪?”李岫不得不提高音量,凑在属下人的耳边问道。
“十字街口。”
远处正有人在舞火鸟,赢得一阵吆喝。
李腾空忽感觉到了什么,抬起头看去,只见有一人正踩着高跷,走在人群头上。
这场景似曾相识,天宝六载的上元节她与薛白也是到东市来,想寻一个药铺。
“就在前面了,他该是要去丰汇行,虢国夫人的产业。”
“带路。”
李岫抬眼看去,只见一家商铺前挂着金币形状的花灯,正要过去,却听得禀报说薛白往前走了。
好不容易拨开人群,出了东市,他正要让手下加快脚程。
“十郎,人被薛徽请走了。”
“该死。”李岫吩咐道,“盯紧薛徽的人,看他们查到什么。”
~~
夜愈深,长安愈亮。
两名女冠领着随从在东市附近走走逛逛,时而抬头看看不远处的望火楼,时而买些布匹、首饰。
末了,她们在小摊边买了两盏花灯,各自要了一支笔,在灯纸上写写画画。
李季兰擅写诗,今年却懒得去雕琢字句,而是执笔轻描,勾勒出了一个少年郎的形象。
李腾空则是陪她打发时间,默写着《道德经》。
“道可道,非常道?”李季兰转头看了一眼,大摇其头,嘟囔道:“上元节,你提着这样一盏花灯?”
“画花灯亦是修行。”
“是我太傻了,使你总拿这种假话敷衍我。”
李腾空心无杂念,只顾写经文,在这灯火阑珊的夜色中显得素雅而独特。
忽然,不远处有歌声传来。
“是薛郎的词。”李季兰站起身来,仔细倾听,之后抬头看向望火楼,呢喃自语道:“他三年前许下志向,要仗义执言、奋不顾身,站在那灯火阑珊处。”
李腾空愣了愣。
耳畔,那歌声已唱到了第二遍,“蛾儿雪柳黄金缕,笑语盈盈暗香去。”
世人都在为之沉醉,却唯她知道,那是他写给她的。
李腾空低下头,接着她抄写的《道德经》,在后面写了一首小诗。
“我有方寸心,无人堪共说。”
“遣风吹却云,言向天边月。”
抬头看去,柳树梢头,一轮明月正圆,清辉遍地。
忽然,
“薛白下来了。”
“有金吾卫跟着,不好拿下。”
“别让薛徽的人看到我们。”
李岫既知薛徽的心意,今夜唯有暂且作罢。
“早晚有护不住他的时候,走吧。”
李腾空回过头看去,只见薛白走到方才那个小摊边,买了一盏花灯,执笔写了一会儿,提着花灯自远走。
~~
清晨,宣阳坊,薛宅。
青岚才安顿了薛白睡下,却听婢子通禀门外有两位女冠求见。
“她们是郎君的好友,也就是郎君外放了一年,你们才不认得她们。”
青岚颇为高兴,亲自到内堂去迎。
“腾空子,季兰子,你们怎来了?”
“我们有桩事想要提醒薛郎。”李腾空道。
她知道薛白昨夜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上,因此,她才会去见李林甫、才会与李岫一起跟着薛白,为的是保护他。
右相府对他的态度还不确定,可能会容忍,可能会除掉,她需要提醒他几句。
青岚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,连忙道:“那我去唤郎君出来。”
“好。”
李季兰见青岚跑开,问道:“腾空子,有镜子吗?我可是熬了一夜。”
“你很美。”
“真的?”
李季兰已发现了内堂上摆着一枚扬州水心镜,于是走了过去。
李腾空一转眼,目光却落在了地上那盏熄灭的花灯上,见上面题着的是一首诗。
那是薛白方才在东市买灯时随手写上去的,当时隔得虽远,她却能感受到他写诗时有些惆怅。
因为丢了官,很不开心吧?
她没忍住,走上前,提起那盏花灯看了一眼。
那是首五言律诗,他的一手颜楷像他的人一样俊逸隽永。
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”
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
“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”
“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。”
~~
一滴泪水划过细腻的脸颊,落在袖子上。
李腾空努力噙住泪,一回头,竟见薛白不知何时已站在她身后了。
她吓了一跳,连忙放下花灯,不知所措。
方才想着心事,不知时间过了多久,薛白似乎已经在那里喊了她很久。但她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失态,干脆快步出了内堂,走进庭院中的小径,吸着鼻子。
“腾空子?”
“那个……季兰子有话与你说。”
李腾空找了个借口,等了一会,李季兰也不懂得来解围,身后没了声响。
她回头瞥了一眼,见到薛白就守在不远处,她又迅速背过身去。
“腾空子。”
“我看到那诗……”
“嗯。”
“我就不该看。”李腾空抹了抹泪,显得有些倔强,“我修我的道,本是自在……偏看到你的心意,反而容易觉得遗憾、委屈……”
“是我不该写那首诗。”
“你乱了我心境。”李腾空没忍住,用哭腔抱怨了薛白一句。
这种蛮不讲理的抱怨,是小女子对最亲密之人才会用的。
她说完才意识到,愈发慌张,强自镇定,道:“我要好好修道,你也要成亲了,不可再写这种诗句。”
“好,昨夜,我……确是想到你。”
“不许。”
“好。”薛白感受她的情绪,缓缓道:“你放心,我只是有感而发,是待好友的态度。”
“嗯,我也只是视你为好友。”
“我这人,最在乎的是自己,始终专注于自己。”薛白说着,逐渐坦诚,“故而我虽心中有你,却不会为你而改变立场、投靠右相府。我首先是我,才会偶尔……有些想念,偶尔。”
“嗯。”李腾空也镇定下来,道:“我也是,首先我是我。我生于相府,修道积德、赎我之罪孽,为我平生所求,我也不会为你改变。”
“好。”
一番话之后,两人反而像更疏远了些。
李腾空听到了身后有脚步声响起,似乎是薛白觉得她足够坚强,于是要离开了。
她不由回过身,问道:“你偶尔……也……也会想念我吗?”
~~
“腾空子?”
李季兰等了一会儿,出了内堂,往庭院里的小径走去,路上很小声地唤了一句。
她其实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知方才李腾空发着呆,被薛白唤了好几声之后跑掉了。也许是太困站在那睡着,被梦魇惊到了?
转过小径,眼前两道人影映入眼帘,李季兰眼眸一瞪,大吃一惊。
“呀。”
“季兰子。”
“你们……我……”李季兰拿手捂在嘴上,假装打了个哈欠,道:“我好困。”
“是啊。”
三人遂往内堂走去。
薛白道:“对了,你们过来找我,有话要说?”
“是,你得罪了我阿爷,又触怒了圣人,明枪易躲,暗箭难防。是否先避一避?”
“避往何处?”
“我们想了一个去处。”李季兰看向李腾空想作眼神交流,李腾空却低着头,她只好道:“王屋山如何?”
“王屋山?”
“灵都观是师父的观邸,谁都不能在其中害你。”
薛白笑着摇摇手,道:“不敢劳玉真公主,我如今无官无职,与人无碍,当不至于有性命之忧。”
“薛郎真罢官了吗?那接下来做什么?”李季兰问道:“写戏文吗?”
“倒是有些想法,该是……炼丹。”
“嗯?”李腾空问道:“你也修道?”
“应该是只炼丹,不修道。”
李腾空修道、习医,对炼丹术也有所了解,并不喜欢那些药材以外的丹药,此时便颇为不解薛白为何会对炼丹感兴趣。
李季兰却很高兴,连忙道:“那我们也帮忙吧?腾空子可有丹炉圣手之称。”
“我哪有。”
“好。”薛白其实已经捉了一个这方面很厉害的道士,却也没推拒她们的好意,“近来得空,还得多多向两位道长请教。”
雪后天晴,才哭过的李腾空心情蓦然好起来。
~~
“阿爷,还有一件事……十七娘去了薛白宅。”
从花萼楼回到右相府,李林甫显得很疲倦,他却还得听李岫禀报上元夜之后发生的诸多事务。
“随他们去吧,你莫管十七娘,两情相悦,你拦得住吗?”
“是。”李岫正要退下,才想起南诏质子之事还没得到明确回答,遂停下脚步问道:“凤迦异之死?”
“元月,有几份奏章。”李林甫道:“群臣请封西岳,圣人已批允了。”
李岫一愣。
“华岳祠已建好,华山道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凿。封禅就在十月,你说南诏叛了?”
“那……”
“叛了也给圣人摁下去。”
“喏!”
李岫终于得了明确的回复,连忙退了出去,赶往议事堂,把李林甫的意思对诸官员吩咐下去。
分为两个方面,一方面传中书政令至西南,着鲜于仲通、张虔陀等官员,务必盯紧阁罗凤,绝不允许南诏出现叛乱;另一方面,严令南衙、京兆府等京城官员,封锁消息,不能让凤迦异叛逃之事闹大……
~~
李林甫难得睡得很沉,但其实到中午也就醒来了。
醒来时,他想到薛白已经丢了官,陈希烈、杨国忠皆已顺服,王鉷之死造成的相位动摇终于过去,让人轻松不少。
至于南诏叛或不叛,这并不重要,因为朝廷早就有所提防,阁罗凤一旦有异心,朝廷在西南的布置足以轻易拿下他。
就在天宝八载,他还命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率军入南诏,取安宁城以及盐井,控制南诏的盐也就控制了其命脉。
换言之,西南不可能有大动荡,没必要对阁罗凤是否有叛心之事小题大作,以免影响到封禅西岳的大事。
这才是他必胜的原因,可惜,薛白等人不懂这些内情。
眼下的问题只在于该牵连到谁为止……张垍?李亨?
李延业之死显然有蹊跷,可以顺着往下查,再掀一场对付东宫的大案。
另外,李林甫也在考虑永王是否适合为储位一事。
“阿爷醒了吗?”院外传来了李岫的声音。
“何事?”
李林甫敏锐地预感到又出事了。
果然,当李岫匆匆进来,手里便拿了一张邸报。
~~
傍晚,薛白醒来,只见有人正坐在榻边的凳子上看着他,是明珠。
“为何这样?怪吓人的。”
“瑶娘担心你的安危,派人来保护你。”
“那也不必如此。”
“我与皇甫小娘子说是来看着你的,她便搬了凳子让我坐。”
青岚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,窘迫道:“我以为看着就是坐在这看着嘛……”
薛白道:“玉瑶是看到邸报了?”
“是,瑶娘说郎君有些过了。”
“给我看看。”
明珠遂从怀中拿出一张邸报递了过来。
薛白其实早就知道内容,但还是再看了一遍。最重要的消息有两则,一说南诏质子凤迦异叛逃,南诏与吐蕃勾结,背叛大唐,已是不争之事实;二说李林甫蒙蔽圣听,粉饰太平,翰林李泌、御史薛白等直臣上元夜进谏,被罢官。
俱为事实。
如薛白与杜妗所言,此事一旦召告天下,哪怕做得再隐秘,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他做的。
这也是杨玉瑶派人来保护薛白的原因。
“郎君近来还是先到虢国夫人府去住一段时日。”明珠劝道。
青岚道:“我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。”
“这次,玉瑶也保不了我,但放心吧,我大抵不会有事。”
薛白这边从容镇定地说完,那边却已有吏员带来了吏部的文书。
“天宝九载制,授薛白海阳县令告身!”
明珠跟在薛白身后出来,听得这一声吆喝,吃了一惊,低下头自思量着也不知瑶娘该有多生气。
“监察御史薛白,司计臣俊言,有应辨才,实堪励俗,故从优秩,今授铜印,俾宰海阳。”
薛白似乎不敢去接告身,推辞道:“可我已经辞官了。”
“并未听闻过薛郎辞官一事,反而恭喜薛县令升官了,海阳县乃潮阳郡之治所,县令可是七品官。”
~~
入夜。
上元节长安城有三个夜晚不会宵禁,这是第二个夜晚。
灯市依旧繁华,没有因为朝堂上的纷争而受影响,市井间反而多了谈资。
这样的夜晚,就连十王宅里的诸王也能够出来逛逛……天宝五载的大案也就是因此而起的。
庆王李琮已经换了衣服,准备带着儿孙们去看看灯市。
但他还在等一个消息。
“大郎。”
“如何?”
“出事了,他被贬往潮阳,傍晚时得的告身,之后便称得了风寒,装病不起。”
李琮问道:“贬往潮阳?他还躲得了吗?”
“不知,大郎是否不去见他为宜,眼下这局面……”
眼下这局面怎么看都是李林甫已经赢了,直谏的几个官员贬的贬、投的投。
但李琮不由总是想起李亨先于自己走到殿中据理力争的场景,那一瞬间,让他觉得自己不如李亨。
“不,我若不去出面,他投靠李林甫就能免于被贬,走吧。”
他知道薛白还有别的选择,皇子很多,且东宫、右相府都在拉拢薛白。从御宴上薛白的态度就能看出来,对他虽有失望,却很平静。
若不去,损失的是他。
李琮遂出了门,去东市看花灯。
他一身普通襕袍打扮,走在人群中远看并不显眼,但近看脸上的疤痕却颇让人触目惊心。
于是,路过一个卖面具的小摊时,他便买了个面具,选了一只猴,虽然他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猴……他的脸就是被猴类抓伤的。
前方有人在舞灯,李琮带着家人避入了一间酒楼,要了个雅间。
而在他身后,有人正不远不近地跟着,寻找着掀起一桩大案的证据。
~~
仅一柱香之后,李琮已是一身小厮打扮,从酒楼后院穿过秘道,走进了一座闹中取静的院落。
他看着十分镇静,心底却隐有些不安。
前方,一道门被推开,李琮整理了衣衫,以及脸上的面具,长吐一口气,迈步走了进去。
薛白竟就在屋内,他本该在家中装病,且被无数人盯着,出来会面是极危险的一件事,而他身边还站着一个气质冷艳的女子。
李琮第一眼没认出这女子是谁,再一看,心中不由讶然,认出她是原来的太子良娣杜妗。
薛白见有人来,竟是伸手在杜妗腰上拍了拍,有个安抚的动作。
“庆王。”
回答薛白的是一张毫无表情的猴面具。
李琮没有说话,在面具的掩盖下,显得很有威严。
但他的背脊已经发凉了。
屋内还有很多个彪悍的大汉,全部站在那,看着薛白与杜良娣卿卿我我,听着他喊“庆王”,让他感到十分危险。
“你们想知道卖命做事能换来什么,今夜我便告诉你们,是从龙之功!这位便是当今圣人之长子,庆王殿下。”
薛白说着,走到李琮面前执礼,道:“还不对庆王见礼?”
“见过庆王!”
李琮想让众人小声些,但这一刻,天潢贵胄的血液在他身体里流淌起来。
他竟是以浑厚而温和的声音道:“诸位壮士既愿与本王生死与共,何必多礼。”
“圣人老了,受奸臣蒙蔽,任用贪官横征暴敛,又听信谗言,一日杀三子。是庆王,收养太子之遗孤,苦心孤诣,欲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之将倾,保大唐盛世之基业。而社稷正统只在庆王一系,何人敢有异言?!”
薛白一番话,屋中众人俱是精神一振,因知自己辅佐的才是大唐正统。
连李琮也振奋起来,感受到自己离储位更近了一步。
他看着薛白那双灼灼的目光,点了点头,缓缓把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。
不需要更多的证明,他这张满是伤疤的脸,就是他身份的最好明证。
“本王问你们,是想要一个面容皎好但昏庸懦弱的储君,还是一个容貌虽有伤却心系黎庶的储君?”
“我等誓为庆王效死!”
听得这样一句并不算整齐的喊话,李琮竟有些感动,郑重道:“本王绝不负诸位壮士!”
“我为庆王引见。”薛白先指了一个面带风霜的汉子,道:“樊牢,曾经在怀州当过捉不良帅。这次便是他查到凤迦异叛逃之事,让我们能提前掌握消息……”
人群中,任木兰不由笑了一下。
她知道,樊牢才不是查到了凤迦异叛逃,事实上就是樊牢带着凤迦异叛逃。
之所以知道,因为就是她扮成奴婢混入李延业府上,偷偷摸进李延业屋中一刀将其结果了,偷出了令牌以及重要证据。
这次到长安,她发现,长安虽好,但长安人不像她能玩命。
至于眼前这个庆王,显然没把她这个小丫头当一回事,看都不看她一眼,只顾着用目光勉励那些壮汉们。
……
见过了这些死士,李琮则与薛白、杜妗单独谈。
“听说哥奴将你贬到潮阳郡了,你可有应对?”
“不是我需要应对。”薛白道,“而是等到哥奴把控不了局面的时候,我们该如何接手国事。眼下不过是破晓前的黑暗罢了。”
“真的?”
李琮一挑眉,惊讶于结果竟比他预想中好得多。
“薛郎能确定?”
“我拿到张虔陀的失踪的奏章了,阿伯可要看看?”
“好。”
李琮很欣慰,薛白终于又与他重新亲近起来。
之后,几封抄录文书便递到了他的面前。
“西南形势,只怕比满朝重臣预想中都糟得多。当此时节,唯阿伯可力挽狂澜、担负起皇长子之重责了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