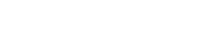洛阳。
烟云卷舒,洛水泱泱,万木森下,千宫对出。
紫微宫前为朝区、后为寝区,安禄山入主之后喜欢住在亿岁殿,除了喜欢宫殿的名字,他每日睁开眼还可望到东南方向的天堂、明堂。
明堂已快要完成最后的改建,他则将在元月初一生日那天登基称帝。当然,那不过是一道仪式,他如今已与称帝无异。
预想中,成为圣人会非常快乐,可真走到了这一步之后,安禄山发现并非如此,相反,他比以前忧虑得多。
他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长子安庆宗的死,在他攻进洛阳不久之后便听闻了此事,安庆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腰斩,身体断为两截之后依旧未死,承受着剧烈的痛苦用双手爬行,拖着半截身子请求禁军给他一个痛快,肠子与脏器流得满地都是,哀嚎声经久不绝。
得到消息时,安禄山正在乾元门接受洛阳官员们的朝拜,因长子惨状而暴虐发狂,突然下令士卒们砍杀那些投降的官员们。于是,青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紫的,身穿各色官袍的人们被关在乾元门内遭到了屠杀,任他们如何求饶哭诉都没有用,伤者倒在地上被反复踩踏,比安庆宗临死前哀嚎得还要久,到最后,只有数百降官在这场屠杀中活了下来,总共杀了七余千人,尸体堆积成山,像是另起了一座血红色的明堂。
树立了威望,并未让安禄山感到满足,他下诏让官员们为他献上美人。可那些美人一个个都无比呆滞,不仅远没有杨贵妃的明艳动人,甚至不如边塞的胡女鲜活。她们眼神里除了恐惧毫无其它。他把她们一个个杀掉,威胁她们在他面前展现出美来,可她们却愈发空洞乏味,只会在他面前瑟瑟发抖。
就连过去的旧部也开始与他愈走愈远,严庄、张通儒、平冽等人总是对他提出各种要求。可他之所以要当圣人,并不是因为没事找事做,他只想要享受。
他没能享受,因为局势已每况愈下。
十余万大军猛攻潼关不克,而洛阳的储粮让人极为失望。
到了洛阳不久,有一日,严庄捧着粮册进了殿,与他说粮食清点出来了。他看过之后非常震惊,终于摆驾去了含嘉仓。
含嘉仓有“天下第一大仓”之称,有四百余个粮窖,粮窖是挖在地下的,呈圆缸形,挖好之后以火烘干,窖底摊着草木灰,上铺木板,再铺上夹着谷糠的两张草席,以免粮食受潮。大窖可储粮一万石以上,小窖亦可储粮数千石,故而安禄山一直听闻含嘉仓储粮五百八十余万石,足够大军支用无忧。
“打开!”
到了一个大窖前,严庄大喝了一声。士卒们上前挖开封木、掀开粮窖上的木板,掀开铺在上方防潮的席子,便显出里面的粮食来。
“这不是有吗?”安禄山凑近了,眨了眨眼。
“圣人请看……掀开!”
严庄挥了挥手,便有人走进粮窖,踩着粮食往前走了几步,任粮食没过他的靴面,但他也没有再陷下去。
遂有一队力士上前,铲出粮窖上层铺着的粮食,只见下面竟还铺着一层木板,掀开木板,一个空空如也的巨大仓窖便出现在了面前。
安禄山用力揉了揉他那豆子大的小眼睛,不敢相信,他可是总在长安听说“东都有粮”才决定先攻打洛阳的,此时不由有种深深的受骗感。
“这是怎么回事?!”
严庄是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,他侧过身,任安禄山将达奚珣招来询问。
安禄山屠洛阳官员之日,达奚珣亦在乾元门,当时活下来的人十不存一,他也险些被杀,是躲在一具尸体下装死才侥幸保住了一条命,此后每次见安禄山都是诚惶诚恐,两股发颤,再也不
敢像以往那样在心里嘲笑安禄山的肥胖与滑稽。
“据臣所知,至少在开元二十四年,含嘉仓的存粮确实是满的。”面对询问,达奚珣思忖着缓缓应答。
“为何是开元二十四年?”严庄问道。
“那正好是在裴耀卿办成‘转漕输粟的第二年,长安昏君下旨罢免了张九龄、裴耀卿。右相……李林甫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,曾经清点过含嘉仓,存粮超过五百万石。”
达奚珣当时正在户部任职,亲自参与了此事,因此非常确定,且印象深刻。
接着,他话锋一转,有了些不确定的语气,道:“此后,存粮必然得一年比一年多。直到天宝八载,超过了五百八十万石,占天下储粮的一半。可此事,臣思来亦感到疑惑。”
“有何疑惑?”
“裴耀卿在运河上修了三个粮仓,江淮船只把粮食运至河阴仓就卸货返航。之后分两路走,东都所需粮食沿洛水至含嘉仓;关中所需粮食沿黄河至集津仓,再开凿十八里山路避过三门峡天险,把粮运至盐仓,由盐仓继续船运至长安。如此,三年内关中储粮便达七百万石,昏君不再至东都就食。”达奚珣道:“可我疑惑的是,运粮之费虽然节省下来了,农夫所种的粮食却未增多,甚至兼并愈烈,隐田、隐户渐多,而田亩日稀。然天宝以来,昏君十年不出长安,糜用日增,挥霍无度,漕运至长安之粮犹源源不绝,而无论灾年、丰年,洛阳储粮依旧只增不减,岂非怪事?”
严庄听懂了,脸色愈发深沉。
开元盛世是不假,可正因是盛世,关中人口急剧增多,田地不堪重负,在最盛世的时候,关中一年尚有四百万石的粮食缺口,昏君犹要带着几十万官员、禁军就食洛阳,怎么随着他越来越怠政、越来越挥霍无度,关中的粮食反而够用了?
转漕输粟之法,只能让天下各地运粮往长安变得方便,至于牛仙客的和籴法,杨国忠的轻货法,也只是节省朝廷征粮的花费,却都不会使固有的粮食增多。
“你是说含嘉仓的粮食也被运到关中了?”
“这……皆有可能。”达奚珣道,“河南常有灾年,常需开仓赈灾,再由江淮漕运粮食补上,也许是赈灾之后便未再运进来。”
他愈发为难,沉吟着,又道:“这些年,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鉷、杨国忠等人相继担任转运使,为昏君运送无数珍宝钱粮,何止亿万贯?若说他们没动这六百万石粮食,我是不信,毕竟谁都知昏君不愿再到洛阳。”
“韦坚?杨慎矜?王鉷?这些人皆被斩了,岂非成了无头冤案?”
“说是无头冤案,确是贴切,这些财宦皆已无头矣。”
“我没与你说笑!”严庄怒道。
忽然,他脑中灵光一闪,泛起一个想法,喃喃道:“莫非那昏君心中知晓,他挥霍的无数钱粮里便包括了含嘉仓的储粮?所以他明知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鉷不可能造反,还是斩杀了他们。”
“还有高仙芝。”达奚珣小声补充道。
“可这是国家的储备粮!他岂可为一己之欲,不顾天下人之死活?!”
严庄转身瞪着那空空如也的巨粮窖,双拳紧攥。
这一刻,面对李隆基留下的乱摊子,这个纵容了叛军烧杀掳掠百姓的反贼竟显得十分正气凛然。完全忘记了这一路而来他们把无数的无辜者杀得血骨累累。
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互相指责轻而易举。
安禄山才不管什么转漕法、和籴法、轻货法,听来听去,听到了最关键的问题,道:“你们是说,昏君把我的钱粮都花光了?!”
“臣猜想是如此。”
“我不信,他那么大方,家底一定很厚!”
安禄山想到粮草不足,心情又开始烦躁起来,命人把一个个粮窖都打开看看。
最可气的是,每掀开一个粮窖,都能看到上面铺着的粮食,让人心怀期待,可只要拿竿子一捅,便知那只有薄薄一层。
安禄山终于忍不住,不顾肚子大得已经快要拖到了地上,亲自奔到一口大粮窖边,喊道:“掀!我不信全都是空的。”
众人一掀,下方又是个巨大的土窖。
“该杀!该杀!”
骂声在窖壁上引起了回音,像是土地用它沉闷的声音呐喊着。
“该杀……该杀……”
安禄山怒气上涌,眼睛却愈发的模糊起来,好像有脓水遮住了视线一般,他看不清粮窖里的景象。
起兵以来,也许是因为太过操劳,近来他一直眼睛不舒服,此时病情忽然恶化到这等地步,身子晃了晃,差点摔了下去。
周围有士卒连忙赶上前来扶他,他却已愤怒到不可遏制的地步,怒吼着一推,将一人推进两丈高的粮窖。
同时,他死死掐住了另一人的脖子,口中发出可怕的呓语,是在用粟特语说自己快看不见了。
“是我……严庄……咳咳……我是严庄……”
过了一会,安禄山眼前稍微清晰了一点,才发现那险些被自己掐死的原来是严庄,他这才松开手。
“怎么办?怎么办?”安禄山问的是眼睛怎么办。
严庄却会错了意,答道:“万不可告诉旁人,会动摇军心的。”
“我知道,还有呢?”
“得派兵马夺取江淮,保证粮草……”
由此,安禄山任命了李庭望为陈留节度使,张通晤为副,出兵东略,意图占据江淮富庶之地,保证长久的粮草供应。
此事一开始还算顺利,谯郡太守望风而降。然而没过多久,河北竟接连战败,连史思明都没能挡住薛白、李光弼、郭子仪等人的反击。之后,薛白更是渡过黄河,联合真源县令张巡、单父县尉贾贲等人收复雍丘,堵在了叛军东略的路上。
听到薛白的名字就让人心烦,但是叛军主力正在潼关鏖战,难以调动。安禄山遂命高尚赶赴开封,希望高尚一人能抵万军之力,击败薛白,打通江淮粮道。等到冬月,登基大典将近,同时叛军粮草即将告罄,偏偏陈留郡却还不明所以,没能攻破雍丘。
安禄山原是想召高尚回来面授机宜,让严庄将洛阳无粮之事相告,商议出办法。结果,严庄却反过来劝他亲征潼关,惹得他大怒不已。当时他甚至拿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严庄。往日他鞭打李猪儿这样的奴才是常有之事,眼下对待身边的重臣却也如此,可见脾气已然失控了。他还命令达奚珣拟旨、叱责严庄、高尚,严庄恐惧无比,不敢再有谏言。
此事之后,薛白突然杀到偃师,斩首高尚。形势急转直下,安禄山连忙命田乾真东向抵御,等到李怀仙兵至偃师,局势稍缓,他遂依着田乾真的谏言,摆酒设宴,邀严庄到紫微宫。
“严卿,上次打了你,我向你赔罪。”安禄山竟再次显得憨态可掬,与发怒时的凶恶模样判若两人,亲自陪了一杯酒,道:“来来,我为你唱歌。”
“圣人厚爱,臣万万不敢当。”严庄脸上鞭伤未愈,却是感动得眼中隐有泪水。
烟云卷舒,洛水泱泱,万木森下,千宫对出。
紫微宫前为朝区、后为寝区,安禄山入主之后喜欢住在亿岁殿,除了喜欢宫殿的名字,他每日睁开眼还可望到东南方向的天堂、明堂。
明堂已快要完成最后的改建,他则将在元月初一生日那天登基称帝。当然,那不过是一道仪式,他如今已与称帝无异。
预想中,成为圣人会非常快乐,可真走到了这一步之后,安禄山发现并非如此,相反,他比以前忧虑得多。
他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长子安庆宗的死,在他攻进洛阳不久之后便听闻了此事,安庆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腰斩,身体断为两截之后依旧未死,承受着剧烈的痛苦用双手爬行,拖着半截身子请求禁军给他一个痛快,肠子与脏器流得满地都是,哀嚎声经久不绝。
得到消息时,安禄山正在乾元门接受洛阳官员们的朝拜,因长子惨状而暴虐发狂,突然下令士卒们砍杀那些投降的官员们。于是,青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紫的,身穿各色官袍的人们被关在乾元门内遭到了屠杀,任他们如何求饶哭诉都没有用,伤者倒在地上被反复踩踏,比安庆宗临死前哀嚎得还要久,到最后,只有数百降官在这场屠杀中活了下来,总共杀了七余千人,尸体堆积成山,像是另起了一座血红色的明堂。
树立了威望,并未让安禄山感到满足,他下诏让官员们为他献上美人。可那些美人一个个都无比呆滞,不仅远没有杨贵妃的明艳动人,甚至不如边塞的胡女鲜活。她们眼神里除了恐惧毫无其它。他把她们一个个杀掉,威胁她们在他面前展现出美来,可她们却愈发空洞乏味,只会在他面前瑟瑟发抖。
就连过去的旧部也开始与他愈走愈远,严庄、张通儒、平冽等人总是对他提出各种要求。可他之所以要当圣人,并不是因为没事找事做,他只想要享受。
他没能享受,因为局势已每况愈下。
十余万大军猛攻潼关不克,而洛阳的储粮让人极为失望。
到了洛阳不久,有一日,严庄捧着粮册进了殿,与他说粮食清点出来了。他看过之后非常震惊,终于摆驾去了含嘉仓。
含嘉仓有“天下第一大仓”之称,有四百余个粮窖,粮窖是挖在地下的,呈圆缸形,挖好之后以火烘干,窖底摊着草木灰,上铺木板,再铺上夹着谷糠的两张草席,以免粮食受潮。大窖可储粮一万石以上,小窖亦可储粮数千石,故而安禄山一直听闻含嘉仓储粮五百八十余万石,足够大军支用无忧。
“打开!”
到了一个大窖前,严庄大喝了一声。士卒们上前挖开封木、掀开粮窖上的木板,掀开铺在上方防潮的席子,便显出里面的粮食来。
“这不是有吗?”安禄山凑近了,眨了眨眼。
“圣人请看……掀开!”
严庄挥了挥手,便有人走进粮窖,踩着粮食往前走了几步,任粮食没过他的靴面,但他也没有再陷下去。
遂有一队力士上前,铲出粮窖上层铺着的粮食,只见下面竟还铺着一层木板,掀开木板,一个空空如也的巨大仓窖便出现在了面前。
安禄山用力揉了揉他那豆子大的小眼睛,不敢相信,他可是总在长安听说“东都有粮”才决定先攻打洛阳的,此时不由有种深深的受骗感。
“这是怎么回事?!”
严庄是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,他侧过身,任安禄山将达奚珣招来询问。
安禄山屠洛阳官员之日,达奚珣亦在乾元门,当时活下来的人十不存一,他也险些被杀,是躲在一具尸体下装死才侥幸保住了一条命,此后每次见安禄山都是诚惶诚恐,两股发颤,再也不
敢像以往那样在心里嘲笑安禄山的肥胖与滑稽。
“据臣所知,至少在开元二十四年,含嘉仓的存粮确实是满的。”面对询问,达奚珣思忖着缓缓应答。
“为何是开元二十四年?”严庄问道。
“那正好是在裴耀卿办成‘转漕输粟的第二年,长安昏君下旨罢免了张九龄、裴耀卿。右相……李林甫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,曾经清点过含嘉仓,存粮超过五百万石。”
达奚珣当时正在户部任职,亲自参与了此事,因此非常确定,且印象深刻。
接着,他话锋一转,有了些不确定的语气,道:“此后,存粮必然得一年比一年多。直到天宝八载,超过了五百八十万石,占天下储粮的一半。可此事,臣思来亦感到疑惑。”
“有何疑惑?”
“裴耀卿在运河上修了三个粮仓,江淮船只把粮食运至河阴仓就卸货返航。之后分两路走,东都所需粮食沿洛水至含嘉仓;关中所需粮食沿黄河至集津仓,再开凿十八里山路避过三门峡天险,把粮运至盐仓,由盐仓继续船运至长安。如此,三年内关中储粮便达七百万石,昏君不再至东都就食。”达奚珣道:“可我疑惑的是,运粮之费虽然节省下来了,农夫所种的粮食却未增多,甚至兼并愈烈,隐田、隐户渐多,而田亩日稀。然天宝以来,昏君十年不出长安,糜用日增,挥霍无度,漕运至长安之粮犹源源不绝,而无论灾年、丰年,洛阳储粮依旧只增不减,岂非怪事?”
严庄听懂了,脸色愈发深沉。
开元盛世是不假,可正因是盛世,关中人口急剧增多,田地不堪重负,在最盛世的时候,关中一年尚有四百万石的粮食缺口,昏君犹要带着几十万官员、禁军就食洛阳,怎么随着他越来越怠政、越来越挥霍无度,关中的粮食反而够用了?
转漕输粟之法,只能让天下各地运粮往长安变得方便,至于牛仙客的和籴法,杨国忠的轻货法,也只是节省朝廷征粮的花费,却都不会使固有的粮食增多。
“你是说含嘉仓的粮食也被运到关中了?”
“这……皆有可能。”达奚珣道,“河南常有灾年,常需开仓赈灾,再由江淮漕运粮食补上,也许是赈灾之后便未再运进来。”
他愈发为难,沉吟着,又道:“这些年,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鉷、杨国忠等人相继担任转运使,为昏君运送无数珍宝钱粮,何止亿万贯?若说他们没动这六百万石粮食,我是不信,毕竟谁都知昏君不愿再到洛阳。”
“韦坚?杨慎矜?王鉷?这些人皆被斩了,岂非成了无头冤案?”
“说是无头冤案,确是贴切,这些财宦皆已无头矣。”
“我没与你说笑!”严庄怒道。
忽然,他脑中灵光一闪,泛起一个想法,喃喃道:“莫非那昏君心中知晓,他挥霍的无数钱粮里便包括了含嘉仓的储粮?所以他明知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鉷不可能造反,还是斩杀了他们。”
“还有高仙芝。”达奚珣小声补充道。
“可这是国家的储备粮!他岂可为一己之欲,不顾天下人之死活?!”
严庄转身瞪着那空空如也的巨粮窖,双拳紧攥。
这一刻,面对李隆基留下的乱摊子,这个纵容了叛军烧杀掳掠百姓的反贼竟显得十分正气凛然。完全忘记了这一路而来他们把无数的无辜者杀得血骨累累。
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互相指责轻而易举。
安禄山才不管什么转漕法、和籴法、轻货法,听来听去,听到了最关键的问题,道:“你们是说,昏君把我的钱粮都花光了?!”
“臣猜想是如此。”
“我不信,他那么大方,家底一定很厚!”
安禄山想到粮草不足,心情又开始烦躁起来,命人把一个个粮窖都打开看看。
最可气的是,每掀开一个粮窖,都能看到上面铺着的粮食,让人心怀期待,可只要拿竿子一捅,便知那只有薄薄一层。
安禄山终于忍不住,不顾肚子大得已经快要拖到了地上,亲自奔到一口大粮窖边,喊道:“掀!我不信全都是空的。”
众人一掀,下方又是个巨大的土窖。
“该杀!该杀!”
骂声在窖壁上引起了回音,像是土地用它沉闷的声音呐喊着。
“该杀……该杀……”
安禄山怒气上涌,眼睛却愈发的模糊起来,好像有脓水遮住了视线一般,他看不清粮窖里的景象。
起兵以来,也许是因为太过操劳,近来他一直眼睛不舒服,此时病情忽然恶化到这等地步,身子晃了晃,差点摔了下去。
周围有士卒连忙赶上前来扶他,他却已愤怒到不可遏制的地步,怒吼着一推,将一人推进两丈高的粮窖。
同时,他死死掐住了另一人的脖子,口中发出可怕的呓语,是在用粟特语说自己快看不见了。
“是我……严庄……咳咳……我是严庄……”
过了一会,安禄山眼前稍微清晰了一点,才发现那险些被自己掐死的原来是严庄,他这才松开手。
“怎么办?怎么办?”安禄山问的是眼睛怎么办。
严庄却会错了意,答道:“万不可告诉旁人,会动摇军心的。”
“我知道,还有呢?”
“得派兵马夺取江淮,保证粮草……”
由此,安禄山任命了李庭望为陈留节度使,张通晤为副,出兵东略,意图占据江淮富庶之地,保证长久的粮草供应。
此事一开始还算顺利,谯郡太守望风而降。然而没过多久,河北竟接连战败,连史思明都没能挡住薛白、李光弼、郭子仪等人的反击。之后,薛白更是渡过黄河,联合真源县令张巡、单父县尉贾贲等人收复雍丘,堵在了叛军东略的路上。
听到薛白的名字就让人心烦,但是叛军主力正在潼关鏖战,难以调动。安禄山遂命高尚赶赴开封,希望高尚一人能抵万军之力,击败薛白,打通江淮粮道。等到冬月,登基大典将近,同时叛军粮草即将告罄,偏偏陈留郡却还不明所以,没能攻破雍丘。
安禄山原是想召高尚回来面授机宜,让严庄将洛阳无粮之事相告,商议出办法。结果,严庄却反过来劝他亲征潼关,惹得他大怒不已。当时他甚至拿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严庄。往日他鞭打李猪儿这样的奴才是常有之事,眼下对待身边的重臣却也如此,可见脾气已然失控了。他还命令达奚珣拟旨、叱责严庄、高尚,严庄恐惧无比,不敢再有谏言。
此事之后,薛白突然杀到偃师,斩首高尚。形势急转直下,安禄山连忙命田乾真东向抵御,等到李怀仙兵至偃师,局势稍缓,他遂依着田乾真的谏言,摆酒设宴,邀严庄到紫微宫。
“严卿,上次打了你,我向你赔罪。”安禄山竟再次显得憨态可掬,与发怒时的凶恶模样判若两人,亲自陪了一杯酒,道:“来来,我为你唱歌。”
“圣人厚爱,臣万万不敢当。”严庄脸上鞭伤未愈,却是感动得眼中隐有泪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