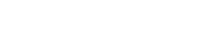“夫君,你这时候,怎么又想起了这些?”张氏问道。
“哎,我们根基不深,陛下想利用我们的名声,来去牵制打压那些勋贵,我献上这十字,本意是能够抽身出来,没想到陛下智谋深远,竟然把咱家的六个女孙,七个儿子都拉到了身边,女孙做妃嫔,儿子做秘书郎。整个把咱家拉上了他的战车。”
“那你可得叮嘱咱们儿子,别惹出事端来。”
“那是自然,我早给他们讲了,人臣之道,奥妙就在进谏的方式方法,直谏是最低效的方法,平民百姓还要个面子哪,何况是九五之尊的陛下。”
“嗯,有你这么说,儿子们应该能够在官场上混的平稳。”
“哎,可陛下不愿意啊,他硬是要将咱们这个女儿、儿子,推到风口浪尖上去,他假意不理朝政,让咱们的女儿、儿子来替他定夺国家政事。好在咱们女儿有才有德,那些人虽然心里不服,但又找不到什么错处。可耐不住陛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,听说陛下为了表彰咱们女儿的贤良淑德,要再盖一座凰仪楼。”
“凰仪楼?这不是要烽火戏诸侯吗?陛下这是安得什么心,这不是把咱家架到火上去烤吗?”
“是啊,这次怕是躲不过去了,不是,他们争权夺利的,拉上咱家干什么?咱就是只想过个安稳日子。”
“夫君,既然避无可避,那就只能迎难而上了。”
“也只能这样了。”刘殷看向屋外泛起的残血夕阳。
刘聪的算盘已经打好了,这个凰仪楼,盖不盖都行,反正自己最近盖了不少的宫殿,还因为温明、徽光两殿的事情,把将作大匠靳陵,给拉出去砍了。
不过,听说,他们靳家有两只女子,一个叫月光,一个叫月华,都是国色天香。
刘聪晃晃脑袋,把这些想法先搁一旁,又看向眼前的棋局,正如刘殷那老狐狸所说,现在汉国的内部,各势力盘根错节,还正要一个明白人来破局。
所以,这次一定要把刘殷那个老狐狸,拖到斗兽场中来,让他和刘渊留下这些开国功臣们,好好的斗一斗。
刘聪在等,他今天特意酒也没喝,女人也没睡,养足了精神,坐在逍遥园李中堂里,等着接下来的对手。
刘聪转头问向身边的中常侍宣怀,“你说今天,还会有人来吗?”
刘聪之所以是问今天,那是因为前面几天来的那些言官都被他一顿板子打了回去,他就是要摆出架势来,让大臣们知道,谁是君,谁是臣。
宣怀没有回答,只是把地上的毯子又摆了摆。
“不必害怕,这里没有外臣,没人说你干政。”
“陛下,依奴才之见,今天怕是要来个大人物了。”
“哦?你看会来什么样的大人物?”
“那一定是那种德高望重的、根基深厚的、颇具清名的。”
“你这奴才,眼光确实不错,可惜啊,是平民之家,终不登大雅之堂,只能屈才在宫中。”
宣怀又没有回答,而是替刘聪把旁边的窗户推开,让风吹得进来。
“风来了,他也来了。把朕的面具拿出来,咱们的大喷子陈元达来了,朕可不想被他喷一脸唾沫星子。”
刘聪伸手接过宣怀递过来的面具。
“陛下,你好像有点怕他。”
“不是怕,是珍惜。一个君王面前,没有一两个敢说真话直话的,迟早要被人做了人肉包子。你没听过吗?师臣者王,友臣者霸,奴臣者亡。有这样的诤臣,是大汉之幸事,朕怕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哪?”
倒不是刘聪有什么特异功能,能够和陈元达心灵感应,而是陈元达那个大嗓门在三里地之外都能听得到。
“你们不要拦我,不就是前几天,几个人都挨打了吗?难道挨了打,该劝谏的就不说了吗?那还叫什么忠肝义胆。王沉你们这些宦官,是不是总在陛下耳边煽风点火?”
“廷尉大人,这可折煞奴才了。奴才哪有那个胆子干政。只是这些天陛下正在气头上,您看是不是等两天,等陛下的气消了,您再来也不迟?”
“这道理能等吗?再等几天,凰仪楼都盖起来了吧?让开,我要面见陛下。”
“陛下正在午休,廷尉大人来得不是时候,总不能惊了陛下的梦?”王沉还是拦着不让进。
“上一边去吧。”陈元达一把就把王沉掀翻在面前,跨过他的身体就迈进了逍遥园。“先皇在时,就赐我特进之权,你一个小小的奴才,也敢阻拦。是谁给你的胆子,难道想向我索贿不成。”
王沉被掀翻后,倒是没着急站起来,而是躺在地上,看着陈元达跨过去,还朝他的脑门啐了一口老痰,然后大步走进园中。
待人走远了,王沉才从笑脸变了颜色,“看什么看,不知道把我扶起来?你们这点眼力见,迟早让人给剁了。”
陈元达风风火火的闯进园中,又要继续往李中堂里闯,却又被宣怀拦了下来。
“廷尉大人,陛下正在休息,是不是劳烦等一等。”
“躲一边去吧。”陈元达再次把宣怀也掀翻在地,“陛下殚精竭虑,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,岂是那种昼寝的朽木?”
“陈爱卿,你说说就行了,不要动手嘛,这也都是爹生妈养的,他们又没有过错,不能因为朕有过错,就去迁怒他人。不迁怒,不二过,陈爱卿以为哪?”
刘聪指着一旁吩咐到,“有点眼色,先帝都待陈大人如师如兄,那朕怎么敢让陈大人站着?”
“谢陛下。”陈元达大模大样的坐在左侧。
“陈卿,你不会也和他们一样,来扫朕的兴吧?”
“臣有几事不明,特来向陛下请教。”
“哦?这天下还有陈卿不明白的事情,快说来听听。”
“臣请问,陛下爱惜自己的女人儿子吗?”
“嗐,朕当是什么问题,自己的女人儿子,自己不爱,难道要别人爱吗?朕为自己的女人修了四十个宫殿,为自己的儿子建了二十座王府,这还不算爱吗?”
“臣听说,圣君都是把国家当做自己的女人那样疼惜,把百姓当做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惜。臣敢问陛下,晋氏横扫三国,兵锋之盛,天下胆寒,何以三十年就国鼎遗失?”
“嗯,好问题。朕记得先帝在时,陈卿与朕讲课时,提起过先秦吴起曾经说过,国家之固,在德不在险。晋氏兵锋虽盛,然勾心斗角,自相屠戮,民不聊生,自然天夺其鼎,归复汉世。”
“那就是说,像晋氏这般强大,如果一味地穷兵黩武,不顾百姓死活,那国祚也是长不了的?”
“这是自然,这不是陈卿一早就教给朕的吗?”
“臣斗胆再问,陛下自比先帝如何?”
“自愧不如,然心向往之。”
“先帝以基业初创,万民疾苦,不敢独享其福,因此着粗布衣,居平阳郡府,后宫皇后妃嫔,既无胭脂又无绸缎,先帝以其害民之利,所以不为。”
“先帝之简朴,朕一向仰慕,不过如今国泰民安,难道不该与民同乐吗?朕不过是造了几个宫殿,也没有像祖龙一样,去修长城营帝陵,怎么诸位爱卿,说得朕像个亡国之君一般?”
“陛下,当年先帝拗不过众大臣,才勉强同意营造南北二宫,如今光极殿前足以大宴群臣,犒赏有功,温明殿足以容纳六宫妃嫔,陛下自登基以来,对外用兵,攻破了洛阳、长安二京,将晋氏皇帝掳了回来。对内兴修宫殿四十余座,这些都是消耗着民力之事,都是损失民心之举。愿陛下察民疾苦,罢土木。”
“爱卿,朕来问你,你会让你的女人睡在大街上吗?你会让自己的儿子和奴仆的儿子挤在一个房子里睡吗?朕要做圣君,但不是做圣人。”
“如果朕都不能兴一宫殿,那么诸卿是不是也不该修了一处宅院又一处哪?难道诸卿所为,就不是消耗民力,丧失民心之举吗?诸卿要求朕做到的,是不是首先得自己做到哪?”
“朕怎么觉得,你们的心思不在这个凰仪楼上,而在你们心中的规矩二字哪?”
“陛下,臣不敢教陛下规矩。当年太宗平诸吕之后,富有四海九州,尚且休养生息,使民安乐,如今陛下所掌汉土,不过是先帝时打下来的平阳、河东二郡,连一州之地都尚未平定,今后用兵之地,自不在少数。臣冒死直言,请陛下罢凰仪楼,以其金银抚慰百姓。”
“反了,反了。你们一个个的圈地盖房子,一个个的比着高的建,也没见谁说一句愧对先帝。朕是万机之主,不过就是在自己的园里想起一座三层小楼,居然被说成什么误国误民。”
刘聪的气突然就顶上了脑门,咔嚓就把面前的桌案一掌劈碎。
“好好好,你不是言必称先帝吗?朕看你是想念先帝了,朕就送你到地下去面见先帝,你亲自去问一问他,大臣们结党营私,该当何罪。来人,给我把他推出去砍了。”
宣怀看到刘聪又陷入了那天鸩杀司马炽的癫狂状态,紧张的吞了口唾沫。
他倒是对这个陈元达没什么好印象,不过谁让人家陈元达不姓陈,而姓高哪?
而且背后站着的可是呼延氏、高氏、卜氏、单氏这四大后部。
一直以来,匈奴王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,娶正妻必须是这四大部族的女子,而刘聪纳了晋人刘殷的女儿刘娥为皇后,这点他们四部是万万不同意的。
这些念头在宣怀脑子里不断的闪过,其他人死不死的,他宣怀真无所谓,但这个陈元达,可不能死,至少不能是他死得时候,自己在身旁。
不然的话,皇帝刘聪为了平息四大后部怒火,多半会把他推出去当替罪羊。
宣怀的脑子飞速的运转,说出了一句有水平的话——把陈大人请下去。
有宦者上前来拉扯陈元达,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有备而来,就在众宦者拉扯他的时候,他从腰间抽出一条铁链来,几个大步跨到一棵大树前。
咔咔咔几下,用铁链把自己和大树绑在了一起。
“臣今天哪里都不去,臣就是死,也是比干那样的忠臣。陛下要因为臣直言,就杀了臣,那就是桀纣一样的昏君。”
众宦者都看向宣怀,宣怀又看向刘聪,刘聪被老头这么一闹,刚才那股子邪火也消散了。
他看向宣怀,问了一句,“你觉得这陈元达该不该杀?”
宣怀没有躲避,而是直接说,“后部强盛,杀之不利。”
“嗯,难得你说一次实话,可现在这老头把朕僵在这里了,要是不杀他,朕的威严何在?”
“刚才皇后娘娘送来一封信。”
“哦?她就在后殿,怎么不来亲自和我说?”
“奴才不知。”
刘聪接过皇后刘娥的信件,里面居然一个字也没有写。
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奴才不知。”
“你又不知了,这是皇后给朕的一个台阶,有了这封信,朕就可以说,是听了皇后的劝谏,知道了愧对贤臣,就可以把这陈老头给放了,只是……”
刘聪看着这张白纸,眼里竟然泛起了泪花,
“她本可以像她那个老狐狸父亲一样,虽在局中,却能事事置身事外。但她还是选择了和朕站在一起。唉。就这么办吧,告诉陈老头,皇后为他求情,朕幡然悔悟,至于信的内容是什么,你自己编一编就行了。”
就这样,陈元达被放了回去。宣怀大笔一挥,还把逍遥园改成了纳贤园,把李中堂改成了愧贤堂。
陈元达却是不服的,他本想着借这个机会,拉皇后刘娥下水,这样就有机会除掉她们了。可这刘娥不但没有恃宠而骄,反而深明大义,这个就有些不妙了。
陈元达越想越气,刘聪他凭什么打破了千年来的规矩,居然敢不娶后部女子为正妻,反娶了同姓之女。
气着气着,陈元达就走进了大将军刘曜的府邸。
“大将军,想不想再戴个白帽子。”
刘曜多鬼啊,立刻装出一副酒醉还没醒的样子,“什么?绿帽子,谁敢给本王戴绿帽子,当本王手中双剑是吃素的吗?”
“大将军,先帝在时,就说大将军是刘家千里驹。如果这天时有变,四大后部,愿听大将军差遣。”
“唉,陈先生,这天啊,万里无云,变不了。明天还是一个艳阳天,我还有几个几女人没睡,今天就不陪你了。”刘曜被两个艳丽女子驾着回到了屋内,不久就传出了不可描述的响动。
“废柴。”陈元达恶狠狠的摔碎了酒杯,起身离开刘府。
“好悬啊,这老头是有病吧,这是跑这里来试探我来了?”
这屋里其实只有刘曜和赵染,而且还是一间作战室,那些响动不过是为了赶走陈元达。
“大王,看来陛下要动手了,争斗就要开始了,也是时候离开了。”
“嗯,确实是一边是四大后部,一边是陛下,哪一边,咱们都惹不起,沾上就是一个死字。”
“大王只要手握兵权,就可坐观成败。至于打哪里,打多久。是要看大王是要做个安乐王爷,还是……”
“怎么讲?”
“如果做个安乐王爷的话,兵出上党,拿下司州、豫州,扫清洛阳附近的晋人余孽,让汉国的疆土扩张到大江之北,这样一来,盘子大了,汉国的底气足了,就算四大后部再想掀起什么风浪,也没有机会了。”
“嗯,如果我还有其他想法哪?”
“那就打长安,而且还要慢慢的打,长安那曲允、索綝不过泛泛之辈,根本不够大王收拾的,但大王却要表现出拼尽全力,却还是棋差一招,要先赢后输。”
“哦?怎么个先赢后输?”
“先赢,就是让陛下看到王爷的实力,后输,就是让陛下知道派给王爷的军马还是不够多,这样就可以通过不断征伐长安,为大王谋得立身之本。”
“将军大才,司马模那个饭桶,他平时重用得到底都是什么人?”
“司马模父子帐下那些人,基本上都是大饭桶和小饭桶,其余不足为虑,唯有一人——陈安,那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毒蛇。”
“哎,我们根基不深,陛下想利用我们的名声,来去牵制打压那些勋贵,我献上这十字,本意是能够抽身出来,没想到陛下智谋深远,竟然把咱家的六个女孙,七个儿子都拉到了身边,女孙做妃嫔,儿子做秘书郎。整个把咱家拉上了他的战车。”
“那你可得叮嘱咱们儿子,别惹出事端来。”
“那是自然,我早给他们讲了,人臣之道,奥妙就在进谏的方式方法,直谏是最低效的方法,平民百姓还要个面子哪,何况是九五之尊的陛下。”
“嗯,有你这么说,儿子们应该能够在官场上混的平稳。”
“哎,可陛下不愿意啊,他硬是要将咱们这个女儿、儿子,推到风口浪尖上去,他假意不理朝政,让咱们的女儿、儿子来替他定夺国家政事。好在咱们女儿有才有德,那些人虽然心里不服,但又找不到什么错处。可耐不住陛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,听说陛下为了表彰咱们女儿的贤良淑德,要再盖一座凰仪楼。”
“凰仪楼?这不是要烽火戏诸侯吗?陛下这是安得什么心,这不是把咱家架到火上去烤吗?”
“是啊,这次怕是躲不过去了,不是,他们争权夺利的,拉上咱家干什么?咱就是只想过个安稳日子。”
“夫君,既然避无可避,那就只能迎难而上了。”
“也只能这样了。”刘殷看向屋外泛起的残血夕阳。
刘聪的算盘已经打好了,这个凰仪楼,盖不盖都行,反正自己最近盖了不少的宫殿,还因为温明、徽光两殿的事情,把将作大匠靳陵,给拉出去砍了。
不过,听说,他们靳家有两只女子,一个叫月光,一个叫月华,都是国色天香。
刘聪晃晃脑袋,把这些想法先搁一旁,又看向眼前的棋局,正如刘殷那老狐狸所说,现在汉国的内部,各势力盘根错节,还正要一个明白人来破局。
所以,这次一定要把刘殷那个老狐狸,拖到斗兽场中来,让他和刘渊留下这些开国功臣们,好好的斗一斗。
刘聪在等,他今天特意酒也没喝,女人也没睡,养足了精神,坐在逍遥园李中堂里,等着接下来的对手。
刘聪转头问向身边的中常侍宣怀,“你说今天,还会有人来吗?”
刘聪之所以是问今天,那是因为前面几天来的那些言官都被他一顿板子打了回去,他就是要摆出架势来,让大臣们知道,谁是君,谁是臣。
宣怀没有回答,只是把地上的毯子又摆了摆。
“不必害怕,这里没有外臣,没人说你干政。”
“陛下,依奴才之见,今天怕是要来个大人物了。”
“哦?你看会来什么样的大人物?”
“那一定是那种德高望重的、根基深厚的、颇具清名的。”
“你这奴才,眼光确实不错,可惜啊,是平民之家,终不登大雅之堂,只能屈才在宫中。”
宣怀又没有回答,而是替刘聪把旁边的窗户推开,让风吹得进来。
“风来了,他也来了。把朕的面具拿出来,咱们的大喷子陈元达来了,朕可不想被他喷一脸唾沫星子。”
刘聪伸手接过宣怀递过来的面具。
“陛下,你好像有点怕他。”
“不是怕,是珍惜。一个君王面前,没有一两个敢说真话直话的,迟早要被人做了人肉包子。你没听过吗?师臣者王,友臣者霸,奴臣者亡。有这样的诤臣,是大汉之幸事,朕怕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哪?”
倒不是刘聪有什么特异功能,能够和陈元达心灵感应,而是陈元达那个大嗓门在三里地之外都能听得到。
“你们不要拦我,不就是前几天,几个人都挨打了吗?难道挨了打,该劝谏的就不说了吗?那还叫什么忠肝义胆。王沉你们这些宦官,是不是总在陛下耳边煽风点火?”
“廷尉大人,这可折煞奴才了。奴才哪有那个胆子干政。只是这些天陛下正在气头上,您看是不是等两天,等陛下的气消了,您再来也不迟?”
“这道理能等吗?再等几天,凰仪楼都盖起来了吧?让开,我要面见陛下。”
“陛下正在午休,廷尉大人来得不是时候,总不能惊了陛下的梦?”王沉还是拦着不让进。
“上一边去吧。”陈元达一把就把王沉掀翻在面前,跨过他的身体就迈进了逍遥园。“先皇在时,就赐我特进之权,你一个小小的奴才,也敢阻拦。是谁给你的胆子,难道想向我索贿不成。”
王沉被掀翻后,倒是没着急站起来,而是躺在地上,看着陈元达跨过去,还朝他的脑门啐了一口老痰,然后大步走进园中。
待人走远了,王沉才从笑脸变了颜色,“看什么看,不知道把我扶起来?你们这点眼力见,迟早让人给剁了。”
陈元达风风火火的闯进园中,又要继续往李中堂里闯,却又被宣怀拦了下来。
“廷尉大人,陛下正在休息,是不是劳烦等一等。”
“躲一边去吧。”陈元达再次把宣怀也掀翻在地,“陛下殚精竭虑,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,岂是那种昼寝的朽木?”
“陈爱卿,你说说就行了,不要动手嘛,这也都是爹生妈养的,他们又没有过错,不能因为朕有过错,就去迁怒他人。不迁怒,不二过,陈爱卿以为哪?”
刘聪指着一旁吩咐到,“有点眼色,先帝都待陈大人如师如兄,那朕怎么敢让陈大人站着?”
“谢陛下。”陈元达大模大样的坐在左侧。
“陈卿,你不会也和他们一样,来扫朕的兴吧?”
“臣有几事不明,特来向陛下请教。”
“哦?这天下还有陈卿不明白的事情,快说来听听。”
“臣请问,陛下爱惜自己的女人儿子吗?”
“嗐,朕当是什么问题,自己的女人儿子,自己不爱,难道要别人爱吗?朕为自己的女人修了四十个宫殿,为自己的儿子建了二十座王府,这还不算爱吗?”
“臣听说,圣君都是把国家当做自己的女人那样疼惜,把百姓当做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惜。臣敢问陛下,晋氏横扫三国,兵锋之盛,天下胆寒,何以三十年就国鼎遗失?”
“嗯,好问题。朕记得先帝在时,陈卿与朕讲课时,提起过先秦吴起曾经说过,国家之固,在德不在险。晋氏兵锋虽盛,然勾心斗角,自相屠戮,民不聊生,自然天夺其鼎,归复汉世。”
“那就是说,像晋氏这般强大,如果一味地穷兵黩武,不顾百姓死活,那国祚也是长不了的?”
“这是自然,这不是陈卿一早就教给朕的吗?”
“臣斗胆再问,陛下自比先帝如何?”
“自愧不如,然心向往之。”
“先帝以基业初创,万民疾苦,不敢独享其福,因此着粗布衣,居平阳郡府,后宫皇后妃嫔,既无胭脂又无绸缎,先帝以其害民之利,所以不为。”
“先帝之简朴,朕一向仰慕,不过如今国泰民安,难道不该与民同乐吗?朕不过是造了几个宫殿,也没有像祖龙一样,去修长城营帝陵,怎么诸位爱卿,说得朕像个亡国之君一般?”
“陛下,当年先帝拗不过众大臣,才勉强同意营造南北二宫,如今光极殿前足以大宴群臣,犒赏有功,温明殿足以容纳六宫妃嫔,陛下自登基以来,对外用兵,攻破了洛阳、长安二京,将晋氏皇帝掳了回来。对内兴修宫殿四十余座,这些都是消耗着民力之事,都是损失民心之举。愿陛下察民疾苦,罢土木。”
“爱卿,朕来问你,你会让你的女人睡在大街上吗?你会让自己的儿子和奴仆的儿子挤在一个房子里睡吗?朕要做圣君,但不是做圣人。”
“如果朕都不能兴一宫殿,那么诸卿是不是也不该修了一处宅院又一处哪?难道诸卿所为,就不是消耗民力,丧失民心之举吗?诸卿要求朕做到的,是不是首先得自己做到哪?”
“朕怎么觉得,你们的心思不在这个凰仪楼上,而在你们心中的规矩二字哪?”
“陛下,臣不敢教陛下规矩。当年太宗平诸吕之后,富有四海九州,尚且休养生息,使民安乐,如今陛下所掌汉土,不过是先帝时打下来的平阳、河东二郡,连一州之地都尚未平定,今后用兵之地,自不在少数。臣冒死直言,请陛下罢凰仪楼,以其金银抚慰百姓。”
“反了,反了。你们一个个的圈地盖房子,一个个的比着高的建,也没见谁说一句愧对先帝。朕是万机之主,不过就是在自己的园里想起一座三层小楼,居然被说成什么误国误民。”
刘聪的气突然就顶上了脑门,咔嚓就把面前的桌案一掌劈碎。
“好好好,你不是言必称先帝吗?朕看你是想念先帝了,朕就送你到地下去面见先帝,你亲自去问一问他,大臣们结党营私,该当何罪。来人,给我把他推出去砍了。”
宣怀看到刘聪又陷入了那天鸩杀司马炽的癫狂状态,紧张的吞了口唾沫。
他倒是对这个陈元达没什么好印象,不过谁让人家陈元达不姓陈,而姓高哪?
而且背后站着的可是呼延氏、高氏、卜氏、单氏这四大后部。
一直以来,匈奴王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,娶正妻必须是这四大部族的女子,而刘聪纳了晋人刘殷的女儿刘娥为皇后,这点他们四部是万万不同意的。
这些念头在宣怀脑子里不断的闪过,其他人死不死的,他宣怀真无所谓,但这个陈元达,可不能死,至少不能是他死得时候,自己在身旁。
不然的话,皇帝刘聪为了平息四大后部怒火,多半会把他推出去当替罪羊。
宣怀的脑子飞速的运转,说出了一句有水平的话——把陈大人请下去。
有宦者上前来拉扯陈元达,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有备而来,就在众宦者拉扯他的时候,他从腰间抽出一条铁链来,几个大步跨到一棵大树前。
咔咔咔几下,用铁链把自己和大树绑在了一起。
“臣今天哪里都不去,臣就是死,也是比干那样的忠臣。陛下要因为臣直言,就杀了臣,那就是桀纣一样的昏君。”
众宦者都看向宣怀,宣怀又看向刘聪,刘聪被老头这么一闹,刚才那股子邪火也消散了。
他看向宣怀,问了一句,“你觉得这陈元达该不该杀?”
宣怀没有躲避,而是直接说,“后部强盛,杀之不利。”
“嗯,难得你说一次实话,可现在这老头把朕僵在这里了,要是不杀他,朕的威严何在?”
“刚才皇后娘娘送来一封信。”
“哦?她就在后殿,怎么不来亲自和我说?”
“奴才不知。”
刘聪接过皇后刘娥的信件,里面居然一个字也没有写。
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奴才不知。”
“你又不知了,这是皇后给朕的一个台阶,有了这封信,朕就可以说,是听了皇后的劝谏,知道了愧对贤臣,就可以把这陈老头给放了,只是……”
刘聪看着这张白纸,眼里竟然泛起了泪花,
“她本可以像她那个老狐狸父亲一样,虽在局中,却能事事置身事外。但她还是选择了和朕站在一起。唉。就这么办吧,告诉陈老头,皇后为他求情,朕幡然悔悟,至于信的内容是什么,你自己编一编就行了。”
就这样,陈元达被放了回去。宣怀大笔一挥,还把逍遥园改成了纳贤园,把李中堂改成了愧贤堂。
陈元达却是不服的,他本想着借这个机会,拉皇后刘娥下水,这样就有机会除掉她们了。可这刘娥不但没有恃宠而骄,反而深明大义,这个就有些不妙了。
陈元达越想越气,刘聪他凭什么打破了千年来的规矩,居然敢不娶后部女子为正妻,反娶了同姓之女。
气着气着,陈元达就走进了大将军刘曜的府邸。
“大将军,想不想再戴个白帽子。”
刘曜多鬼啊,立刻装出一副酒醉还没醒的样子,“什么?绿帽子,谁敢给本王戴绿帽子,当本王手中双剑是吃素的吗?”
“大将军,先帝在时,就说大将军是刘家千里驹。如果这天时有变,四大后部,愿听大将军差遣。”
“唉,陈先生,这天啊,万里无云,变不了。明天还是一个艳阳天,我还有几个几女人没睡,今天就不陪你了。”刘曜被两个艳丽女子驾着回到了屋内,不久就传出了不可描述的响动。
“废柴。”陈元达恶狠狠的摔碎了酒杯,起身离开刘府。
“好悬啊,这老头是有病吧,这是跑这里来试探我来了?”
这屋里其实只有刘曜和赵染,而且还是一间作战室,那些响动不过是为了赶走陈元达。
“大王,看来陛下要动手了,争斗就要开始了,也是时候离开了。”
“嗯,确实是一边是四大后部,一边是陛下,哪一边,咱们都惹不起,沾上就是一个死字。”
“大王只要手握兵权,就可坐观成败。至于打哪里,打多久。是要看大王是要做个安乐王爷,还是……”
“怎么讲?”
“如果做个安乐王爷的话,兵出上党,拿下司州、豫州,扫清洛阳附近的晋人余孽,让汉国的疆土扩张到大江之北,这样一来,盘子大了,汉国的底气足了,就算四大后部再想掀起什么风浪,也没有机会了。”
“嗯,如果我还有其他想法哪?”
“那就打长安,而且还要慢慢的打,长安那曲允、索綝不过泛泛之辈,根本不够大王收拾的,但大王却要表现出拼尽全力,却还是棋差一招,要先赢后输。”
“哦?怎么个先赢后输?”
“先赢,就是让陛下看到王爷的实力,后输,就是让陛下知道派给王爷的军马还是不够多,这样就可以通过不断征伐长安,为大王谋得立身之本。”
“将军大才,司马模那个饭桶,他平时重用得到底都是什么人?”
“司马模父子帐下那些人,基本上都是大饭桶和小饭桶,其余不足为虑,唯有一人——陈安,那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毒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