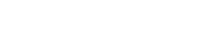陈元达回头望了一眼中山王府的匾额,鼻子哼了一下。
“哼,胸无大志的东西,我本欲辅佐你成就霸业,你却只想做个老兵卒。”
陈元达往前刚走几步,就被一辆马车拦住了去路,一个身高九尺的小厮从车上站起来,小跑几步,来到陈元达面前躬身一礼。
“河内王请廷尉大人过府一叙,还请大人赏光。”
“哼,你这小厮倒是生得高大,但有什么用?还不是一个低等下人。”
“廷尉大人,不知可否听过白龙鱼服的故事。小人固然不值一提,但在这街巷之间,四下无人,小人取大人的性命,易如反掌。”
“你……你敢这么和我说话,你家王爷都尊称我一声先生。”
陈元达向后倒了一步,仰头看着这个和刘曜差不多魁梧的汉子,这小厮竟然也有如此的胆识。
“大人不是说过吗?臣畏君者,有所惧也,君畏臣者,有所求也。小人无惧无求于大人,而杀了大人,自然有其他红了眼的大人给小人好处和名声。”
“罢了。”陈元达一抚胡须,欣然上车,在车上撩起帘子来问,“不知壮士姓名?”
“王平,人贱无字。家母就希望小人平平安安的。”
“好名字,这世道啊,平安才是福。你知道你们大王请我去干什么吗?”
“小人只做分内事,只听该听的。还请大人不要陷小人于危难。”
“倒是有些见识,只可惜啊,你既不是太原的王氏,又不是琅琊的王氏,前路已经注定。”陈元达长叹了一声。
王平没有回话,只是专心赶车,七拐八拐的车就停到了河内王刘粲的府门口,刘粲正带着一众府僚在那里等候。
见马车停住,刘粲紧跑了两步,挤到王平身内,从马车上取下板凳,亲自堆着笑脸,掀开车帘。
“陈师父,请。”
“老朽怎么敢劳烦大王的大驾。”
“哎,陈师父,今日没有大王和廷尉,只有陈师父和粲弟子。”
“哈哈,大王未曾忘本,不像有些人,注定是个老卒。”
“粲也是一介老卒,一壶老酒、一匹老马,足以此生,不敢奢望更多。”
“哦?哪你还?”
“当然是给师父顺顺气。”
“你知道我心中有气?”
“师父心里装得都是忧国忧民,怎能无气。”
“哦?这话你也敢说,就不怕?”
“父知子直,子知父明,有什么不敢的哪?”
“你是想借我这个老东西,演一出戏给陛下看?”
“师父说是,便是了。弟子不敢反驳。”刘粲罕见的行了一个规矩的弟子礼。
“你手下蓄养着这般威武的死士,怕是所谋不浅吧?”陈元达指向一旁拴马的王平。
“师父误会了,王平只是生得长大,却是一个读书人,是王府记账的管事。”
“记账的?也有这般胆识?还说要手刃了老夫,以彰其姓名?”陈元达不平的看着王平。
“他向来是喜欢唬人的,不想到师父也被他唬住了。别说杀人了,见人杀只鸡,他都能晕死过去。”
“哦?是吗?大王在此时请老朽过府,不怕生出什么瓜葛?中山王可是给老朽装了一回糊涂。大王不会也如此吧?”
“曜叔也是没办法,才高遭忌,功高遭妒,克二京之功,功高足以震主。自然有不少人,早就打了他的主意。”
“这克长安的功劳,本来应该是大王的,为何让给中山王?”
“记得师父给弟子授《韩非子》时,曾经说过,如果有五把刀,最先钝的,一定是那把最锋利的。弟子自然不去做那把最锋利的,劝师父也别去。”
“大王也知道了?大王若不弃,老朽愿为大王作马前卒,扳倒大王面前的这块大石头。”陈元达指着面前的一块拦住二人去路的奇石。
“师父,弟子说过,弟子不做最锋利的刀。这石头若是挡了我的去路,我绕开便是了。”
“我不与人争,该是谁的,便是谁的,如今我汉国虽百战皆胜,然地未增一郡,土未扩一县,空耗国力,我心不安,请师父教授弟子破解之法。”
两人进了密室,刘粲进去就拎起海碗,连干三碗,以表诚意。
“这……”
“师父可是有难言之隐?此间只有你我师徒二人,话不传六耳,师父大可放心。”刘粲又添了一碗,依旧诚意满满。
“石勒取襄国,占邯郸,营邺城,最近听说连三台之上的残兵也扫了干净,刘演落荒而逃,此可以为外援。”
“拓跋建三城,从农事,兴汉化,似有王者之相,不宜轻取,此时攻刘琨,只会徒增伤亡。”
“洛川诸顽,各倚坞堡,坚壁清野,不易攻取。”
“师父的意思是,让弟子再攻长安?”刘粲靠着桌边,又仰起一碗。
“正是,如今会稽公已崩,晋氏必立嗣皇,秦王已为太子,即位顺理成章。这次机会,大王可不能再错过了。”
“有理、有理,还是师父看得长远。”刘粲嫌海碗实在不过瘾,拎起坛子灌了起来。
“大王似乎对此事兴致不高?大王……大王?”陈元达久久没有听到刘粲的回话,再一看刘粲已经四仰八叉的醉倒在地上,还抱着那个酒坛子梦魇。
“哎,饭桶啊。”陈元达气得一甩袖子出了密室,刚出密室,他就愣住。
他看到了一个不该看到的人,皇太弟刘乂,这里是河内王府,还是最紧要的密室,皇太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
“高大人,别来无恙啊?”刘乂喊了陈元达的本姓。
“殿下,您?这……”陈元达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就感觉一斤的讶堵在了嗓子里一般,什么完整的话都说不出。
“廷尉,看起来很意外啊?”
先呼姓,又呼官,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样子,说明刘乂已经很生气了。
“这里,这里恐怕不是说话的地方吧?”陈元达打量着密室外的这间套房,是在假山里的一处机关中。
“很方便。”刘乂一鼓掌,刚才还在拴马的王平走到了陈元达面前。“没错,王平是我的人,我安插到河内王府中,看看这家伙有没有异心。结果谁知道,白费了力气,只不过是个酒蒙子。”
“是,是,殿下神机妙算,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自然不是臣能够揣摩的。”
陈元达擦了擦汗,如果自己真的死在了河内王府,那么没人会怀疑到一直以仁孝闻名的刘乂,反而会觉得刘粲像是那个一言不合就动刀子的人。
“不要紧张,长宏兄,”刘乂的手轻轻的拍了拍对方颤抖的大腿,“虽说孤很不满意你的自作主张,但孤也不是那么心胸狭窄的人。只是孤在你心中,竟然一点份量也没有吗?先找了中山王曜,又找了河内王粲,怎么孤要是不亲自来,下面你是不是还要把刘易、刘骥这些王爷的府邸都走一遍?”
“臣,臣不敢。臣怕给殿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“陈师父,当年你教孤要韬光养晦,你也看到了,这就是韬养的结果,那人封了一个儿子又一个,若不是畏惧我四大后部的实力,只怕早就对孤动手了。”
“殿…殿下,臣知错了,臣不该去进谏,就该让陛下越发张狂才好。”
“那个女人,师父怎么看?”
“不愧是刘家女,听闻刘殷有七子,七子各传一经,但刘娥无论和哪个兄弟,辩哪部经书,都无一败绩。”
“这才是孤真正担心的,若那人真的是沉迷女色,又加上五石散,必没有寿数。若他还是使假哪?就像他当年骗刘和一样。谁能想到他暗中把所有人都凝聚到了一起。”
“老臣派了多名美男,屡次和她偶遇调情,却都被她识破杖杀,这女子幸亏是个女子。”
“这种蠢办法,对付蠢女人还行,对付刘娥?她能耐得心来钻研七经,还耐不住些许的寂寞吗?”
“请殿下指点。”
“你们哪,总想着往人身上泼脏水,可遇到这么一个知书达礼的人 ,就没了心思,也不知道养你们有什么用?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埋怨,孤没有去那人面前为你求情?”
“臣……臣不敢。”
“那就是有了?陈师父,快醒醒吧?你就是改姓了汉姓,通晓了易理,能和名士坐而论道,醉而谈玄,那你也还是后部人,四大后部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”
“臣……臣没有那个心思。臣只是想……”
“孤自然知道,你若是真有那个换主的想法,王平早送你去见先帝了。你只是想利用这些王爷想夺权的心,把刘殷一家除掉,这样那人就不得不再纳我四大后部的人为后了。陈师父,你把问题想简单了。”
“请殿下赐教。”
“先生不是常说,臣畏君者亡,君畏臣者兴吗?”
“正是,这是古老相传的经典。自古贤君无不如此。”
“屁,先生真是读书读傻了。君王为万机主,大臣的人头像韭菜一样,割了一茬,自然会再长出一茬。君王所畏惧的一直都不是臣子,而是形势,是天命。”
“殿下的意思是?”
“孤没有什么意思?只记得先生提起过,什么样的异象,是什么人在作祟。先生,读书啊,要细读,礼法才是杀人最快的刀。”
“是,是,老臣一定细读。”
许久不闻回音。
“殿下已经走了,大人起来吧,地上凉。”
王平过去把陈元达搀扶起来,将他扶出府去,请上马车,送回府去,这才回来。
“殿下,殿下。可以醒了,都走了。”王平走进密室摇醒了刘粲。
“王平,你做得不错,继续保持。都能把刘乂那个胆小鬼,请到府上,用了不少功夫吧?”
“不敢当,都是殿下的计策高妙,属下只是依计而行,换谁去都一样的。”
“哎,不一样,谁能和你一样有嫪毐一的下面?还有张仪的上面。”
“殿下又拿属下寻开心了。”
“现在太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?都拉拢了一些什么人?”
“他的功夫做得很深,有些可能连我也瞒着。就现在来看,刘景刘延年这两位元勋宿将,已经非常坚定的站了过去。还有会稽公那些大臣,尤其是晋氏成都王司马颖的智囊卢志,也被他收到了帐下听说还打算表荐个太弟府的重要官位。”
“卢志?我听说过这个人,这人还有个流传很广的小故事呐。他第一次见到大名士陆机,就直楞楞的问,哎,那个谁,陆逊、陆抗这俩反贼,和你什么关系啊?”
“也是够楞的。”
“可不是嘛,那陆机是何等人物,连晋武帝的面子都敢不给,能惯着他这臭毛病,直接就回怼,啊,就和你与那背汉求荣的卢毓、卢班的关系一样。把这卢志的脸给臊得呀,再也不敢小看江南士人了。”
“殿下真是博闻广记,又何必装出一副沉迷酒色的样子哪?”
“没有办法啊?谁让爷爷起兵造了反,非要来当这个皇帝,搞得一家人,父不父,子不子,兄不兄,弟不弟。晋氏八王之乱的教训就摆在眼前,那是一点都没吸取啊,我看哪,说不定哪天,汉国就玩完了。不如先享受几天,免得到时候透露不知道被谁摘了去。”
“殿下既然有此心思,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,何不与陛下说明哪?”
“父皇?他能不知道?别看他一天到晚,除了酒就是女人,他什么不清楚?还用我说?只是爷爷走得太急,好多事情没处理完,就留下个烂摊子。你听到我刚才和陈元达说得话了吧?五把刀,最先钝的,是最锋利那一把。”
“殿下,真不打算和那些大臣们走动走动,臣听说连河间王易、济南王骥都走动起来了。”
“那是俩大傻子,到时候说不定被谁卖了换钱哪,不用去理会他们,我专心做我的孤臣,一个没有脑子,只有服从的孤臣。”
“那长安那边?”
“自然还是交给曜叔,我在晋阳坑了他一次,算是还他个人情。”
“殿下就不怕他和石勒一样坐大?”
“那又能怎么办?父皇防我像防贼一样,不得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啊?”
“哼,胸无大志的东西,我本欲辅佐你成就霸业,你却只想做个老兵卒。”
陈元达往前刚走几步,就被一辆马车拦住了去路,一个身高九尺的小厮从车上站起来,小跑几步,来到陈元达面前躬身一礼。
“河内王请廷尉大人过府一叙,还请大人赏光。”
“哼,你这小厮倒是生得高大,但有什么用?还不是一个低等下人。”
“廷尉大人,不知可否听过白龙鱼服的故事。小人固然不值一提,但在这街巷之间,四下无人,小人取大人的性命,易如反掌。”
“你……你敢这么和我说话,你家王爷都尊称我一声先生。”
陈元达向后倒了一步,仰头看着这个和刘曜差不多魁梧的汉子,这小厮竟然也有如此的胆识。
“大人不是说过吗?臣畏君者,有所惧也,君畏臣者,有所求也。小人无惧无求于大人,而杀了大人,自然有其他红了眼的大人给小人好处和名声。”
“罢了。”陈元达一抚胡须,欣然上车,在车上撩起帘子来问,“不知壮士姓名?”
“王平,人贱无字。家母就希望小人平平安安的。”
“好名字,这世道啊,平安才是福。你知道你们大王请我去干什么吗?”
“小人只做分内事,只听该听的。还请大人不要陷小人于危难。”
“倒是有些见识,只可惜啊,你既不是太原的王氏,又不是琅琊的王氏,前路已经注定。”陈元达长叹了一声。
王平没有回话,只是专心赶车,七拐八拐的车就停到了河内王刘粲的府门口,刘粲正带着一众府僚在那里等候。
见马车停住,刘粲紧跑了两步,挤到王平身内,从马车上取下板凳,亲自堆着笑脸,掀开车帘。
“陈师父,请。”
“老朽怎么敢劳烦大王的大驾。”
“哎,陈师父,今日没有大王和廷尉,只有陈师父和粲弟子。”
“哈哈,大王未曾忘本,不像有些人,注定是个老卒。”
“粲也是一介老卒,一壶老酒、一匹老马,足以此生,不敢奢望更多。”
“哦?哪你还?”
“当然是给师父顺顺气。”
“你知道我心中有气?”
“师父心里装得都是忧国忧民,怎能无气。”
“哦?这话你也敢说,就不怕?”
“父知子直,子知父明,有什么不敢的哪?”
“你是想借我这个老东西,演一出戏给陛下看?”
“师父说是,便是了。弟子不敢反驳。”刘粲罕见的行了一个规矩的弟子礼。
“你手下蓄养着这般威武的死士,怕是所谋不浅吧?”陈元达指向一旁拴马的王平。
“师父误会了,王平只是生得长大,却是一个读书人,是王府记账的管事。”
“记账的?也有这般胆识?还说要手刃了老夫,以彰其姓名?”陈元达不平的看着王平。
“他向来是喜欢唬人的,不想到师父也被他唬住了。别说杀人了,见人杀只鸡,他都能晕死过去。”
“哦?是吗?大王在此时请老朽过府,不怕生出什么瓜葛?中山王可是给老朽装了一回糊涂。大王不会也如此吧?”
“曜叔也是没办法,才高遭忌,功高遭妒,克二京之功,功高足以震主。自然有不少人,早就打了他的主意。”
“这克长安的功劳,本来应该是大王的,为何让给中山王?”
“记得师父给弟子授《韩非子》时,曾经说过,如果有五把刀,最先钝的,一定是那把最锋利的。弟子自然不去做那把最锋利的,劝师父也别去。”
“大王也知道了?大王若不弃,老朽愿为大王作马前卒,扳倒大王面前的这块大石头。”陈元达指着面前的一块拦住二人去路的奇石。
“师父,弟子说过,弟子不做最锋利的刀。这石头若是挡了我的去路,我绕开便是了。”
“我不与人争,该是谁的,便是谁的,如今我汉国虽百战皆胜,然地未增一郡,土未扩一县,空耗国力,我心不安,请师父教授弟子破解之法。”
两人进了密室,刘粲进去就拎起海碗,连干三碗,以表诚意。
“这……”
“师父可是有难言之隐?此间只有你我师徒二人,话不传六耳,师父大可放心。”刘粲又添了一碗,依旧诚意满满。
“石勒取襄国,占邯郸,营邺城,最近听说连三台之上的残兵也扫了干净,刘演落荒而逃,此可以为外援。”
“拓跋建三城,从农事,兴汉化,似有王者之相,不宜轻取,此时攻刘琨,只会徒增伤亡。”
“洛川诸顽,各倚坞堡,坚壁清野,不易攻取。”
“师父的意思是,让弟子再攻长安?”刘粲靠着桌边,又仰起一碗。
“正是,如今会稽公已崩,晋氏必立嗣皇,秦王已为太子,即位顺理成章。这次机会,大王可不能再错过了。”
“有理、有理,还是师父看得长远。”刘粲嫌海碗实在不过瘾,拎起坛子灌了起来。
“大王似乎对此事兴致不高?大王……大王?”陈元达久久没有听到刘粲的回话,再一看刘粲已经四仰八叉的醉倒在地上,还抱着那个酒坛子梦魇。
“哎,饭桶啊。”陈元达气得一甩袖子出了密室,刚出密室,他就愣住。
他看到了一个不该看到的人,皇太弟刘乂,这里是河内王府,还是最紧要的密室,皇太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
“高大人,别来无恙啊?”刘乂喊了陈元达的本姓。
“殿下,您?这……”陈元达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就感觉一斤的讶堵在了嗓子里一般,什么完整的话都说不出。
“廷尉,看起来很意外啊?”
先呼姓,又呼官,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样子,说明刘乂已经很生气了。
“这里,这里恐怕不是说话的地方吧?”陈元达打量着密室外的这间套房,是在假山里的一处机关中。
“很方便。”刘乂一鼓掌,刚才还在拴马的王平走到了陈元达面前。“没错,王平是我的人,我安插到河内王府中,看看这家伙有没有异心。结果谁知道,白费了力气,只不过是个酒蒙子。”
“是,是,殿下神机妙算,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自然不是臣能够揣摩的。”
陈元达擦了擦汗,如果自己真的死在了河内王府,那么没人会怀疑到一直以仁孝闻名的刘乂,反而会觉得刘粲像是那个一言不合就动刀子的人。
“不要紧张,长宏兄,”刘乂的手轻轻的拍了拍对方颤抖的大腿,“虽说孤很不满意你的自作主张,但孤也不是那么心胸狭窄的人。只是孤在你心中,竟然一点份量也没有吗?先找了中山王曜,又找了河内王粲,怎么孤要是不亲自来,下面你是不是还要把刘易、刘骥这些王爷的府邸都走一遍?”
“臣,臣不敢。臣怕给殿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“陈师父,当年你教孤要韬光养晦,你也看到了,这就是韬养的结果,那人封了一个儿子又一个,若不是畏惧我四大后部的实力,只怕早就对孤动手了。”
“殿…殿下,臣知错了,臣不该去进谏,就该让陛下越发张狂才好。”
“那个女人,师父怎么看?”
“不愧是刘家女,听闻刘殷有七子,七子各传一经,但刘娥无论和哪个兄弟,辩哪部经书,都无一败绩。”
“这才是孤真正担心的,若那人真的是沉迷女色,又加上五石散,必没有寿数。若他还是使假哪?就像他当年骗刘和一样。谁能想到他暗中把所有人都凝聚到了一起。”
“老臣派了多名美男,屡次和她偶遇调情,却都被她识破杖杀,这女子幸亏是个女子。”
“这种蠢办法,对付蠢女人还行,对付刘娥?她能耐得心来钻研七经,还耐不住些许的寂寞吗?”
“请殿下指点。”
“你们哪,总想着往人身上泼脏水,可遇到这么一个知书达礼的人 ,就没了心思,也不知道养你们有什么用?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埋怨,孤没有去那人面前为你求情?”
“臣……臣不敢。”
“那就是有了?陈师父,快醒醒吧?你就是改姓了汉姓,通晓了易理,能和名士坐而论道,醉而谈玄,那你也还是后部人,四大后部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”
“臣……臣没有那个心思。臣只是想……”
“孤自然知道,你若是真有那个换主的想法,王平早送你去见先帝了。你只是想利用这些王爷想夺权的心,把刘殷一家除掉,这样那人就不得不再纳我四大后部的人为后了。陈师父,你把问题想简单了。”
“请殿下赐教。”
“先生不是常说,臣畏君者亡,君畏臣者兴吗?”
“正是,这是古老相传的经典。自古贤君无不如此。”
“屁,先生真是读书读傻了。君王为万机主,大臣的人头像韭菜一样,割了一茬,自然会再长出一茬。君王所畏惧的一直都不是臣子,而是形势,是天命。”
“殿下的意思是?”
“孤没有什么意思?只记得先生提起过,什么样的异象,是什么人在作祟。先生,读书啊,要细读,礼法才是杀人最快的刀。”
“是,是,老臣一定细读。”
许久不闻回音。
“殿下已经走了,大人起来吧,地上凉。”
王平过去把陈元达搀扶起来,将他扶出府去,请上马车,送回府去,这才回来。
“殿下,殿下。可以醒了,都走了。”王平走进密室摇醒了刘粲。
“王平,你做得不错,继续保持。都能把刘乂那个胆小鬼,请到府上,用了不少功夫吧?”
“不敢当,都是殿下的计策高妙,属下只是依计而行,换谁去都一样的。”
“哎,不一样,谁能和你一样有嫪毐一的下面?还有张仪的上面。”
“殿下又拿属下寻开心了。”
“现在太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?都拉拢了一些什么人?”
“他的功夫做得很深,有些可能连我也瞒着。就现在来看,刘景刘延年这两位元勋宿将,已经非常坚定的站了过去。还有会稽公那些大臣,尤其是晋氏成都王司马颖的智囊卢志,也被他收到了帐下听说还打算表荐个太弟府的重要官位。”
“卢志?我听说过这个人,这人还有个流传很广的小故事呐。他第一次见到大名士陆机,就直楞楞的问,哎,那个谁,陆逊、陆抗这俩反贼,和你什么关系啊?”
“也是够楞的。”
“可不是嘛,那陆机是何等人物,连晋武帝的面子都敢不给,能惯着他这臭毛病,直接就回怼,啊,就和你与那背汉求荣的卢毓、卢班的关系一样。把这卢志的脸给臊得呀,再也不敢小看江南士人了。”
“殿下真是博闻广记,又何必装出一副沉迷酒色的样子哪?”
“没有办法啊?谁让爷爷起兵造了反,非要来当这个皇帝,搞得一家人,父不父,子不子,兄不兄,弟不弟。晋氏八王之乱的教训就摆在眼前,那是一点都没吸取啊,我看哪,说不定哪天,汉国就玩完了。不如先享受几天,免得到时候透露不知道被谁摘了去。”
“殿下既然有此心思,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,何不与陛下说明哪?”
“父皇?他能不知道?别看他一天到晚,除了酒就是女人,他什么不清楚?还用我说?只是爷爷走得太急,好多事情没处理完,就留下个烂摊子。你听到我刚才和陈元达说得话了吧?五把刀,最先钝的,是最锋利那一把。”
“殿下,真不打算和那些大臣们走动走动,臣听说连河间王易、济南王骥都走动起来了。”
“那是俩大傻子,到时候说不定被谁卖了换钱哪,不用去理会他们,我专心做我的孤臣,一个没有脑子,只有服从的孤臣。”
“那长安那边?”
“自然还是交给曜叔,我在晋阳坑了他一次,算是还他个人情。”
“殿下就不怕他和石勒一样坐大?”
“那又能怎么办?父皇防我像防贼一样,不得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啊?”